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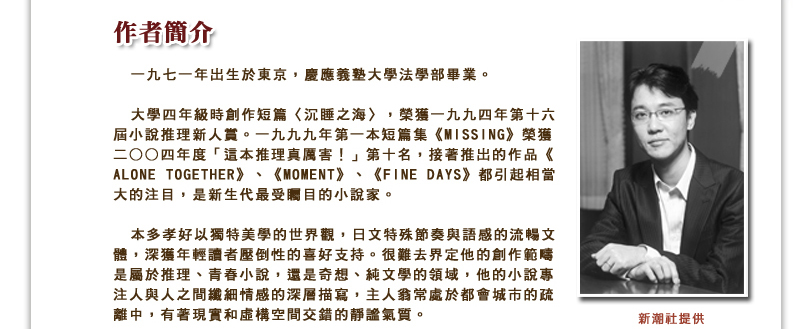

張開眼睛,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搖曳的火光。背部凹凸不平的堅硬感覺,讓我知道自己躺 「你醒了。」 火焰的對面,響起一個陌生少年的聲音。 「這是哪裡?」 好不容易擠出的聲音極其嘶啞,實在很丟臉。 「你看就知道,這裡不是天堂。」 我坐了起來,回頭看著背後的懸崖,露出一絲苦笑。 「看來,我失敗了。」 少年配合我的冷笑話,發出乾笑聲。 「怎麼可能成功。稍微會游泳的人,就不可能死得了。」 少年把手上的樹枝丟進火裡。 冬天時,每天只小露一下臉的太陽早就西沉了,眼前是一片沒能吞噬我生命的茫茫大海,黑 「要不要再挑戰一次?」 看我正望著背後的懸崖峭壁,少年揶揄地問。 「不必了。」 我在嘴裡曖昧地回答,把手放在篝火旁。冬天的海風吹著身上的濕衣服,身體已經冷到骨子裡。 眼前的景象實在令人不堪。一個跳海自殺失敗的三十歲男人,被素昧平生的少年救起,正坐在 「對了,」 少年好像突然想起什麼,拿起腳邊的眼鏡。 「這是你的嗎?」 「對。」 「哇,那糟了,這邊的鏡片已經破了。」 「沒關係,反正只是裝飾用的。」 「是嗎?」 少年把玩著手上的眼鏡。我看著倖存的鏡片反射出的火光。 「我該向你道謝。」 「道謝?」 少年想了一下,然後才好像理解這句話中的涵意,輕輕笑了笑。 「不需要道什麼謝,但你既然想死,應該有更乾脆的方法。比方說上吊啦,或是服安眠藥之類 「對喔!」 「既然這樣,下次可不可以請你用那些方法?這一帶的風評本來就很差,外地人經常來這裡跳 「你是這裡的人?」 「對,我就住在附近。」 我搜尋著遙遠的記憶。那時候,這一帶沒有人煙,不過,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現在, 「下次我會小心。」 說完,我雙腳用力站了起來。雖然有點搖晃,但似乎還可以走路。 「你要去哪裡?」 少年也站了起來,訝異地抬頭看著我。 「我也不知道,還沒決定。」 「你準備四處流浪,尋找自己的葬身之地嗎?」 少年用鼻子哼著氣,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我轉身準備離開,少年從背後叫住了我。 「等一下。」 回頭一看,少年用下巴指了指我剛才坐的地方。 「你最好坐在那裡把衣服烘乾,你這個樣子,連巴士也不能坐,這個季節,也找不到計程車。」 「我用走的。」 「白癡喔。你知道從這裡到鎮上有幾公里嗎?你現在這個樣子,一定會累倒在路邊。同樣是死, 我又苦笑了一次,坐回原來的位置。 少年心滿意足地頷首,一言不發地看著漆黑的大海。 從上衣內袋裡拿出香菸。包裝盒雖然濕了,但裡面的香菸似乎還能抽。 拿起柴火點了支菸,和少年一起眺望著大海。 茫茫的大海黑壓壓的,不時駛過海岸的汽車的車前燈,像鐳射燈般映照著洶湧的浪濤。 我甚至無力思考,是否該慶幸自己還能活到現在。 不知道過了多久,少年突然轉過頭來。 「喂,」 「幹嘛?」 「你為什麼尋死?」 「你幹嘛問?」 「隨便問啊。」 少年嘔氣地回答後,把手上的木塊丟進火勢變小的篝火。木塊好像是被海浪打到岸上的浮木。木 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想開口談這些事。可能是單調的波濤聲和搖曳生姿的火苗讓我變 「因為,」 「什麼?」 「我害死了人。」 少年想了一下我說的話,隨即搖搖頭,似乎放棄了思考。 「是喔。」 他笨拙的樣子很好笑。 「你想聽嗎?」 少年把脖子轉過來,用力點點頭。 我看著大海,思考著要從哪兒說起。如果話說從頭,就要回到二十年前。 我把變短的菸蒂丟進篝火。 「我有二十年沒回來這裡了。」 「咦?叔叔你以前也住這裡嗎?」 「那時候,我的年紀比你現在還小。」 年幼時,我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父母開了一家小旅館,我和他們一起,渡過了平淡無奇的少年時 我父母的車子為了閃避突然跑出來的少年,撞毀了護欄,衝進了大海。無論是駕駛座上的父親,還是 姑姑和姑丈有兩個孩子,因此,那個家對我來說,絕對不可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雖然姑姑和姑 從古到今,對愛飢渴的孩子能夠採取的手段始終如一。不是鬧彆扭,就是格外乖巧。兒時的我,選擇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別人一樣開始談戀愛後,這種性格依然沒變。即使面對情人時,即使在肌膚之親 畢業後,我當了老師。並不是因為我對這個職業充滿熱情,而是因為我對社會這個開放的世界心生畏 我就職的那所公立高中,升學率在縣內數一數二。老師們雖然熱心輔導學生的課業,對同事的隱私卻 姑姑死後,我離開了姑姑家,開始一個人住。環境固然改變了,但狀況依舊沒變。我靠著父母的遺產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結識了佐倉京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