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價:24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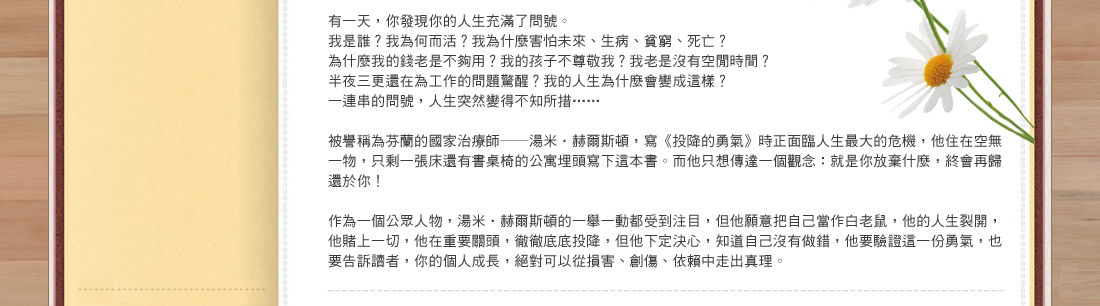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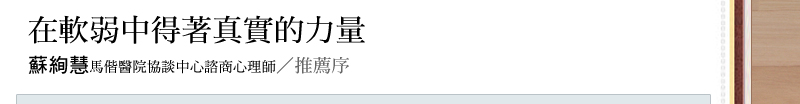
《投降的勇氣》是一本好看的書。好看的,不只這是一本貼近生命的書,而是可以幫助人和自己深層、真實的對話,從中面對自己,療癒自己。也就能理解,何以赫爾斯頓被譽為「國家治療師」。 赫爾斯頓是一位芬蘭的心靈治療師,執業已三十多年,我在他的字裡行間仍看見他持續以充滿愛的心與具有洞察的眼和生命對話,用一種近距離的方式和讀者沉穩的談著那些,在人心中那最隱微的心靈角落所深藏的軟弱、失落與傷痛,還有懼怕、不安與粗暴。當然,他也像一個慈藹的智者引領著讀者一步一步的走過自我整合的道路,邁向成長。 台灣受西方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影響下,人們總是汲汲營營盤算著自己的人生,如何的付出如何的收成,又計算著怎樣可以走一條捷徑獲取自己要的成功目標。而在長期的社會文化與歷史運作下,我們的家庭也影響我們,讓我們以為一個強者是不該有軟弱,也不該有缺點與限制的。甚至,認為軟弱是羞恥的,軟弱代表一個人的無能,與失敗。以致,我們奮力追求無可挑剔的完美強人,以為只要追求到了完美地位,我們就能擺脫軟弱與羞愧的記憶與經驗。 這是一連串的謬思,也是導致我們活得越來越破碎與分裂的原因。真實的我們,心靈可能早已傷痕累累了,卻還是要故作堅強,假裝一切無傷無痛無影響。我們沒有勇氣對自己誠實,自然也會要別人不要對自己誠實。我們不允許自己軟弱,自然也不准他人可以軟弱。 我們因此活得無法再與自己靠近,也無法與他人的生命靠近。 這樣的堅強,不是從內在生出的真實力量,而是為了抵抗外在眼光與評價的防護盔甲,為了保護內在不安與恐懼的心,即使盔甲剛硬、沉重,也不能卸下。 赫爾斯頓透過這本書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有愛,這愛會陪伴與帶領我們認識真實的自己,愛中沒有羞愧,愛裡也沒有懼怕。愛可以讓我們走在人生最低落處時,生長出對生命的擁抱與慈悲。 而我這麼深深相信。當我們承認了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沒有那麼堅強時,我們才能開始不拋棄生命,不試圖再靠堅強來杜絕自己所需要的愛與接納。也不在夜深人靜時,再惡毒的唾罵自己怎麼可以軟弱、沒用,怎麼可以渴望愛與擁抱。 雖然這是一本來自芬蘭治療師所寫的著作,也是一本蘊含著基督教信仰意涵的書籍,但我閱讀起來卻有許多生命連結,也認為這是一本跨越文化的人世智慧,即使您可能不是基督教信徒,都可能藉此與您的內在神性相連,也尋回您人生失落已久的勇氣、愛,與心,真正成為有生命氣息的「人」,真實的成為自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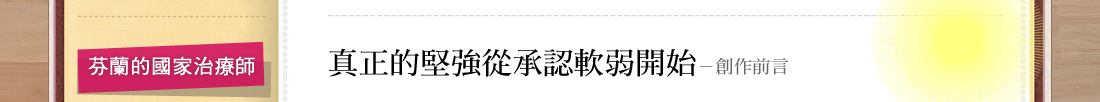

受夠了堅強 後來這個年輕的美人懷孕了。夏季某一晚,她臣服在那雙沉思的眼眸下,一夕之間,天翻地覆:兩人的浪漫史變成了悲劇,綁住了他們兩個。女孩仍想要盡情享受青春,感覺自由自在,征服無數的異性,體會美麗容顏的種種好處。可是太早了,太快了,人生緊緊攫住了他們。 女孩的母親以嚴厲聞名,所以當然不能跟她透露懷孕的事。於是年輕人和女孩決定結婚,馬上結婚,以免有人起疑。 我來到人間純屬意外,是他們夏日縱情後驚人可恥的結果。我會知道是因為我父親有一次在談話中觸及這個話題──隨後就又說到他的從軍經驗,任我因為這消息而目瞪口呆。 雖然婚結得倉促,但是這對新婚夫婦卻打造了一個美麗的家,歡喜迎接新生兒降臨。我後來知道我外婆得意洋洋的抱著她的外孫給鄰居看。我父親是攝影師,有上百張的相片照的是我父母跟我,鍾愛的小男嬰。在我們的家庭電影中,我看見的似乎是五○年代理想家庭的生活:我父親,高大英俊,打領帶、戴灰色軟呢帽;我母親,魅力十足,而且對時尚的嗅覺絕對敏銳,推著一輛嬰兒車。兩人似乎都很健康快樂。 其實他們的關係卻像定時炸彈──他們缺少了從戀愛過渡到相愛所需要的元素。我母親年紀太輕,就是沒辦法放棄吸引男人注目的小小嗜好;她珍視自己的魅力,為滿足自己而運用魅力。我父親的醋意越來越濃,開始藉酒澆愁,他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無法再重拾戀愛的喜悅。起初父親只在社交場合喝酒,也不過量,但是幾年之後,就越喝越兇了。也可能他喝酒是要報復母親的賣弄風情。漸漸的,一家之主不復存在。 我父親在認識我母親之前就有一分小小的事業,婚後夫妻兩人攜手同心,經營得倒也有聲有色。他第一次酒駕被捕,入獄服刑三個月,她承擔起更多責任,在生意和家庭中的地位都更加重要。而他越沒有地位,酒就喝得越兇──但即使總是醉醺醺的,他仍準時上班,沒多久全鎮的人都知道了他的酗酒問題。儘管我們很自信沒有人知道我家的秘密,其實大家已經管我們叫酒鬼的家了。 我父親沉溺酒鄉二十年,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因酒駕被判刑,一次是他被迫就醫。 我想像中的童年家庭是沒有人在家──雖然父母親人在,心卻不在。我的父母親滿腦子都是自己的痛苦和不滿足的需求,所以壓根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們的孩子;畢竟自己都沒有的東西又怎能夠給別人呢?他們需要協助;可是,我們家是誰都不會開口求助的。最要緊的是保持美好的假象:就是因為沒有一樣好,才要拚命裝出個樣子來。恥辱必須不計代價隱藏起來。我記得有一次,那年我十四歲,在電影院裡等著電影開場,我後面坐了一群人,他們談起了某個笨蛋酒鬼捅的樓子。等我明白他們談論的人居然是我父親,我簡直是羞辱到了極點。 多年來,恥辱成了我們家庭的一分子。我們從不討論這個新成員;我們從不讓它引起的悲傷、憤怒、尷尬顯露在外。我看不見自己的寂寞、憂愁、羞恥,因為沒有人看得見它。我甚至還學會了拿我父親的酗酒來說俏皮話。我們調整自己來適應恥辱,而恥辱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要求越來越多的空間。那就好像是一隻河馬突然搬進了我家客廳。這樣子形容最能凸顯恥辱的龐大以及殘酷的荒謬──我們需要更費心費力才能假裝它不在那兒。 我把父親輸給了酒精,我母親則把丈夫輸給了酒精,而她自己沒多久也快消失不見,因為她必須承擔起養家的全部責任。她越來越強悍,但她的強悍卻來自於矢口否認軟弱;換句話說,她變得受夠了堅強。這時,她憑直覺尋求支援和安慰,而她找到了我,她的長子。她開始跟我推心置腹,跟我討論,需要我。她不再當我是小孩子;她只是透過不滿足的需求在看我。我的童年結束了,我也變得受夠了她那樣的堅強。 結果這個家變成了無父無母的一個家,每個成員都必須想盡辦法求生。我母親跟我成了盟友;我們一起嘲笑我父親──倒是一點也不難,因為他的種種行為實在很難教人尊敬。我在家裡的角色是在情感上補償我母親失去丈夫的遺憾。我很機伶,隨時迎合別人的需要。我安慰母親,傾聽她的牢騷,再和我父親討論她想要傳達的想法。 家裡唯一的淨土是鍋爐室。我就在那裡第一次執業。背後有中央加熱系統低聲運作,我和我父親或是母親進行我相信是很深刻的討論;我的目的是幫助父親戒酒,挽救婚姻。我在鍋爐室裡成了家庭輔導員。說來諷刺,我父親也習慣把酒瓶藏在這個房間裡;他對加熱系統的問題報告得越多,他的人也就醉得越厲害。 我的輔導員工作完全根據一個十五歲大的孩子能有的智慧和經驗。有一次,我姑媽問我長大要做什麼,我跟她說我要當心理醫師。其實,我早就是了。我從圖書館借來了成堆的書,努力研究佛洛伊德、佛洛姆之流,其實根本看不懂多少──誰教它是專業的文學呢。我還涉獵了中國哲學,以林語堂為導師。(我記得是在早晨讀的,換作一般人這個時間應該兩腳腳趾踩在毛茸茸的地毯上,心平氣和的休息,然後才出門去面對新的一天的挑戰。) 等我十七歲了,我父母也得到了一個必然的結論:他們開始思索離婚。在那個年代,離婚比起今天來要複雜許多(如果真能這麼比的話),所以我父母徵詢我的看法。我覺得他們該離婚嗎?我記得在仔細思考之後,我的答覆是應該──而他們果然離婚了,半年之後。酗酒一事沒有人再提起。無巧不巧,家破人散之後,我母親也變成了酒鬼。離婚後十年,她自殺了。 我們一家破裂之後,無論我走到哪裡,我都動手幫助別人,因為這是我在家裡就扮演的角色。十九歲那年,服完了兵役,我開始求學,心裡想最終我會得到自由。我最後決定要主修神學,卻發現自己在七○年代後期擔任酗酒輔導員。當時我並不明白我在選擇生涯時,其實是在摸索自救的道路。我更不知道我心裡還帶著童年時丟下不管的需求──不曾得到滿足,因此和以前一樣的咄咄逼人。 工作的關係,讓我接觸了明尼蘇達模式的成癮治療,以及十二步驟計畫。後來我又接觸了支援酗酒者的成年孩子的運動──當時仍是一個新的現象──我覺得好像終於回家了。而一種強大的內在過程也油然而生,這個過程後來轉變成探索過去之旅,挖掘我的傷痛是從何開始的,找出我真正的自我來。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別人需要的角色,可是經由這個過程,我找到了自己。 感情上的痛苦並不是無法治癒的疾病,可是以我而言,從童年創傷恢復卻必須耗時多年,而且極盡辛苦。十幾歲出頭就擔當家中的治療師,我逐漸看不見真正的自我,而是以別人的需求來界定自己。我不能需要別人、信任別人,也不能軟弱,而這種求生的策略讓我無法面對我所經歷的痛苦。一直到長大成人了,我才逐漸領悟這一點影響我有多深。我察覺到這種痛苦成了障礙,阻斷了美好的人生,而我必須跨越這個障礙。 我鼓起勇氣凝視鏡中的自己──但鏡中卻空無一人。我這才發現,即使我現在已過了而立之年,我卻根本沒活過。我只是在苟延殘喘。我開始一點一滴的從多年的痛苦之後覺察到一直在尋覓什麼:我的真面目。在我家裡,從沒有人當我是真正的那個我,所以我長大就成了某某人。而在這個某某人之後是一個他的存在從沒有人目睹過的人;一個被悲哀、恐懼、不安全感壓住的人;一個在年紀太小時就承擔了過大的責任的人。此外我也發現了相當的怒氣得不到宣洩,以及龐然的孤寂。 漫長的治療、自助團體、心理戲劇三管齊下,我的個性終於又從根深柢固的羞恥感中浮上表面。我明白了我不是壞人;我這一輩子都覺得壞,因此才失去了整個童年以及童年之後的時光。 我從生涯選擇中找到了我尋尋覓覓的協助,可是我並沒有放棄當治療師的工作。我不再汲汲營營於找到真面目,因為我已經找到了,我在過程中重新和我真正的本質接軌,而我現在可以用自己的經驗來把別人看得更清楚。 這本書在我的祖國很暢銷,和我的第一本書《客廳裡的河馬》一樣──而我簡直無法形容我的驚訝。我的第一本書出版後,沒多久我就發現別人幫我冠上了「國家治療師」的稱號,我身不由己變成了公眾人物,對一個曾深受羞恥之苦的人來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忍了下來,甚至還學會了去領略它的滋味,雖然我總喜歡這麼想,我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寫了下來,可是出名卻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現在知道一路下來我必然是寫出了也說出了一種共同的經驗:我們在自己和別人身上認出的傷口,以及在發現的旅程上共享的喜悅。 我很開心的說今天我覺得很好。我結婚了,第二度結婚,第一次婚姻給了我三個好孩子。我的長子近來也加入了我妻子和我共有的家庭事業,繼續我畢生的志業,而我另外兩個孩子似乎也尾隨他的腳步。這趟旅程十分漫長,但曾是我極大的軟弱現在似乎轉變為我極大的力量。我能有今天都要歸功於我的軟弱;軟弱是我最大的財富,也是我最大的福氣。 所以我才會針對軟弱寫了那麼多。所以我才會說真正的力量必定是以承認軟弱開始;要成長就一定要先衷心接受自己的軟弱。事實上,真正的成長意味著我們越長越渺小,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有更深刻的體認。謙卑在這種成長上是必要的元素。面對我們的軟弱,我們也會了解到我們是不能孤獨而活的:我們需要別人;我們需要心靈交流。軟弱讓我們敞開來接受愛,來接受我們身為人類最需要的東西。而只要我們需要愛,我們就需要上帝,祂不因為我們軟弱就不愛我們,反而就是愛我們的軟弱。上帝的愛總是尊敬我們的內在自我。上帝的愛把我們創造成獨一無二的個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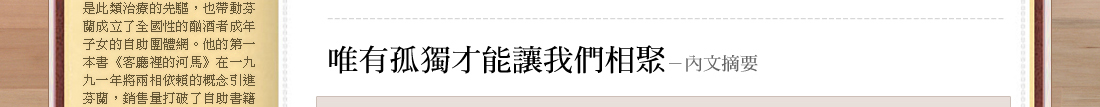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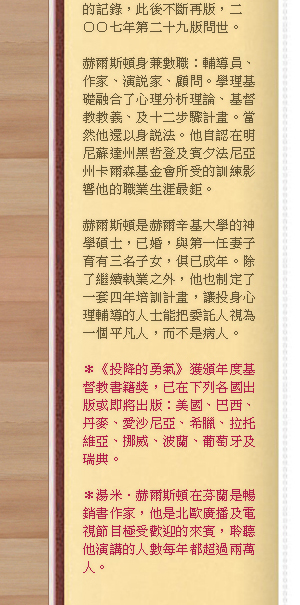
今天,婚姻破裂成了常態,而不是例外。我們發現越來越難讓兩人的結合維繫下去。結果,我們似乎失去了走入婚姻的勇氣。我們寧選其他的安排,因為那麼一來比較容易脫身。 是什麼讓我們這麼難建立持久的聯繫並且謹守一段感情?在無數的例子裡,婚姻失敗都是因為一方無法尊敬另一方是獨立的個體。這份尊敬牽涉到承認並欣賞另一半的自主權,並且給予空間。 愛會滋養並且鼓舞個人的性格。它盡力創造一個氣氛,讓每一方真實的自我都能生存,讓我們可以體驗並表達我們性格的全部深度。唯有尊敬雙方的個人性──他或她的完整性和自主權──得到實踐,愛才能在一段感情中茁壯繁茂。這樣的感情才能讓我們在對方眼裡是真正的我們。 要是我們不能欣賞另一半的自主權,我們就是無力或拒絕去看見另一半的真面目。我們的認知被童年或青少年期起就得不到滿足的需求──跟我們父母有關的需求──給扭曲了。我們不能指望由我們的配偶來滿足這些需求。 可是我們不滿足的童年需求卻沒有隨時間而減弱或是消失於無形,而是在我們心裡抱窩,絕對真實,而且壓迫著我們,矢志要求滿足。我們的過去開始用不實際的期望來損壞我們的現在,不再能夠分辨出那是童年時的需求。這些需求在眼前變成了不可理喻的苛求,通常對象都是我們最親近的人──最常見的是配偶。我們也許會反抗個人的界限,不尊敬我們重要的另一半是個獨立的成人。我們把過量的責任加諸他們身上,指望他們能驅散我們的傷心難過。我們和配偶並不是平等的夥伴關係,而是為了我們自己的目的來剝削這個關係,表現的形式有許多種,比方說我們會死纏著配偶不放,期待他或她能提供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成人能夠供應的安全及保護。 生命是我們沒辦法交給別人代理的責任。我們長大了之後,就絕不能再期望別人當我們的母親或父親;我們必須要做自己的父母。我們必須長大,變成獨立的個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承擔責任,如果需要,也願意正視我們的過去。 我們的過去是愛情裡的輔輪 「妳在哪裡,堅強的女人?我在這裡,妳虛弱的夥伴。」 一個拒絕長大的人會排斥所有的責任。他找別人──配偶最為常見──找個願意分擔更多責任的人。他是怎麼做到的? 憑直覺。他送出下意識的信號,那些符合他要求的人自然接收得到。比方說,男人可以送出無助的信號,透露出他在找一個願意照顧他並且扮演母親角色的女人。如果把這些秘密的信號解讀出來的話,很可能就像這樣:「妳在那裡,堅強又有力的女人?我在這裡,妳虛弱、無助的夥伴,我是永遠也離不開妳的男人,事事都得依賴妳!我要妳幫我負起責任來。我需要妳因為我不想長大。我需要妳當我的媽。把我護衛在妳的羽翼下!」 在下意識的層面,這些秘密信號會打動某個正在找人來照顧的女人。她可能早就有照顧別人的漫長歷史,從年幼時照顧父親或母親就開始了。照顧別人成了她的定位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她只有變身為別人依賴的人才能和別人接軌。假如她一開始就被別人看成是一個總是會幫忙並且諒解他人的人,那她也會學著如此看待自己。她缺少為自己著想、留意自己需求的能力,只是一味注意別人,總是關心別人是否安好,犧牲自己的需求來迎合別人的需求。 任何女人接收到無助男人送出的信號,都應該會警鐘大作。不過無我的女人卻聽不見警鐘──就算聽到了,她也會誤以為是婚禮的鐘聲。她一頭就栽進了愛河,覺得終於找到了此生最愛。可是這一對男女卻沒辦法以平等的夥伴關係一起生活,反而是過去未解的課題扭曲了他們看待彼此的方式。下意識裡,他們的過去會破壞他們的現在。他們並不是愛上了對方,他們是愛上了終於可以讓童年需求滿足的希望。 「你在哪裡,軟弱的人?過來這裡讓我控制你。」 再談談另一個例子:一個女人長大了卻無法與自己的母親認同。這個做母親的或許排拒她的女兒,當她是一個威脅到她的競爭者。說不定是這個做母親的始終不能接受自己是個女人,始終沒學會珍惜她的女性特質。她很可能是童年性虐待的被害人,一直沒有機會克服痛苦的經驗。她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壓抑事關虐待的一切記憶及感覺,因而不知道虐待的後果仍然影響著她的性別。她不喜歡體內的這個女人,所以也不喜歡在女兒身上看見的女人。她無法疼愛自己的女兒,不喜歡跟她親近,而且很少碰她、抱她,或是表現母愛。她也許把女兒照顧得很好,可是只是出於責任感。因為她心中懷著內疚,愧於不能愛她的孩子,所以她反而盡量當模範母親,一切都「照書上來」,其實她仍和自己的孩子很疏遠。可是因為罩上了一層完美的面紗,所以母女間的距離始終沒有人注意到。 做女兒的沒有機會從母親那兒學到當女人是怎麼回事。少了親密關係,她沒辦法從母親那找到她需要接觸以及仿效的女性對照物。她和自己的女人角色一直沒有接觸,不能去愛、去尊敬心中的那個女人,因為她母親忽視了那個女人,也排斥那個女人。 也可能做父親的在行為舉止中告訴孩子他並不尊敬他的妻子。父母的關係最大的特色可能是缺乏真正親密,結果影響了父母親情緒上的健全。做父親的把怒氣和挫折發洩在妻子身上。他以數不清的方式讓妻子知道她有多無能、多白痴、多低等。原因可能是這個做父親的並不承認內心的軟弱,反而學會了去輕蔑它。他很可能把女性的溫柔當成是軟弱,所以他攻擊妻子心中的女人,以他對待自己軟弱的不敬來對待她。這麼一來,他也教導女兒不尊重她自己。做女兒的從父親的批評和輕視中解讀出自己身為女人的價值,學到了她是沒有價值的人。 接納自己女性特質的女人很清楚身為女人的價值,對她而言,身為女性是一種自然的存在狀態,不是什麼她需要彌補的威脅或缺憾。她樂於和男人共同生活;她和丈夫立足點平等,即使她和他不一樣。他們的平等是建立在對彼此本色的尊敬上,無論是兩人的相異處或是相同處。 上述的例子裡當女兒的不能和母親認同,又缺少了健康的女性楷模,等她長大之後,她就會變成心理分析理論中的「有陰莖的女人」。她模仿父親無情的舉止,想要彌補自己不是男人──她相信唯有這個性別才有價值、才值得欣賞。無法以女人的身分和男人展開平等的夥伴關係,她尋求的配偶會是一個讓自己被控制、被支使得團團轉的人。他們的關係永遠是持續不斷的權力角逐,形之於外的模式就是不停的衝突和爭吵。女方覺得必須強勢──強勢到足以抑制男方的陽剛對照,免得她必須面對自己的女性特質。 這樣的愛情是不會有真正的親暱的,因為男女雙方對彼此而言都不是男人女人。他們都覺得空虛,對兩人的關係覺得不自在,因為兩人的需求都沒有滿足。在他們的權力競逐中,他們把自己的煩惱怪罪到對方頭上,這就讓他們更難找到親密關係。 只要他的妻子在場,做丈夫的就覺得不快樂,可是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要他願意接下悲慘男人的角色,這一對男女就可以不用去面對他們的痛苦。可是如果這個男的開始質疑自己的角色,拒絕由他的妻子來界定兩人的關係,他就會創造出危機來,而這個危機可以帶來成長──逼得伴侶雙方無路可走,只能正視他們的痛苦,加以處理。否則的話,他們可能只剩下走上離婚一途。 除非我們看見自己,否則看不見別人 唯有彼此尊敬,一段感情才會茁壯;換句話說,伴侶雙方必須看見對方的本來面目。少了這份尊敬,愛情就不是兩人結合,而是利用對方。要結合當然需要一個可以結合的人,所以雙方都必須與自己真實的自我連結。我們必須了解我們自己真正的性格,才能認清並且尊敬別人的性格。所以第六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來了:唯有孤獨才能讓我們相聚。 要是我們不清楚自己的過去,我們無可避免就會一直活在過去。如果我們被個人的過去所監禁,我們真實的性格就不會誕生。我們的過去扭曲了我們看自己的角度,也扭曲了我們看別人的方式。要看清別人的真實面,首先我們必須真正看見自己──而為了要看見自己,我們就必須移除遮擋了視線的障礙。我們必須面對過去,察覺出過去隱藏了什麼。 面對過去的話,我們得一肩挑起責任來。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能再把自己未解決的問題怪罪到別人頭上。我們自己的不幸不能再推給朋友、同事、鄰居、超了我們的車的人──而且我們也不再埋怨自己的人生沒有變得更美好都要怪我們的伴侶不肯改變。 一肩挑起責任需要我們承認自己的不完美與不完整。只要我們對自己的缺點盲目,否認我們需要長大,我們就很難不把自己的不快樂都推給伴侶。可是通常我們都要等到痛苦承受不住了,才會承認;我們都是等到痛苦變得太強烈,逼得我們不得不去正視,這個時候我們才會願意承認。 假如我們指望別人來扛起我們的痛苦,就不會有成長。再回到先前那個無情的女人和軟弱可悲的先生那個例子。如果男的繼續扮演他現在的角色,他的妻子就沒有理由要去正視她的問題;她對權力和控制的幻覺並沒有受到威脅。而這個男的也沒有成長,沒知覺到他肩負了別人的痛苦,除非他能夠認清自己。 正視自己的痛苦絕不是什麼愉快的經驗。與其面對我們自己的不完整,怪罪別人要方便得多。可是承認自己的不完整卻是讓我們學會尊敬別人的不二法門。除非我們做到了尊敬別人,否則我們的感情就會缺少真正的親暱,我們也無法和重要的另一半共營平等的關係。 對他人缺少尊重通常都脫不了膚淺的自我認識。我們對自己知道得越少,就越覺得有必要批評、月旦、譴責別人。新約說得好,我們看見鄰居的眼裡有刺,卻看不見自己眼裡有梁木。我們批評別人、譴責別人,為的是避免正視自己的軟弱。我們輕視別人,其實我們真正輕視的是我們心裡不願承認的東西。我們對別人的評斷其實評的是我們自己,多過了我們瞧不起的人。我們想要迴避的內心邪惡越大,我們譴責別人的需要就越強烈。我們越是深入認識自己,就越能夠尊敬別人。 -摘自《投降的勇氣》部份內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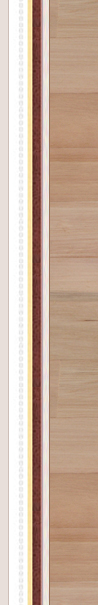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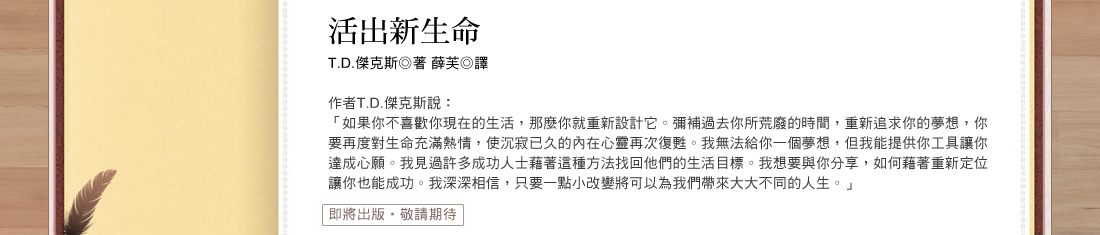


 一開始似乎是十全十美。有個英俊的年輕人,波浪般的金髮覆著額頭。還有一位每個男孩都仰慕的黑髮美女。我猜我父親很得意能夠贏得鎮上最美的女孩子芳心。說不定我母親,在十九之齡,也很得意能夠迷住樂隊的金髮吉他手,那個笑容充滿深意、眼神渴盼的男人。生命充滿了希望。
一開始似乎是十全十美。有個英俊的年輕人,波浪般的金髮覆著額頭。還有一位每個男孩都仰慕的黑髮美女。我猜我父親很得意能夠贏得鎮上最美的女孩子芳心。說不定我母親,在十九之齡,也很得意能夠迷住樂隊的金髮吉他手,那個笑容充滿深意、眼神渴盼的男人。生命充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