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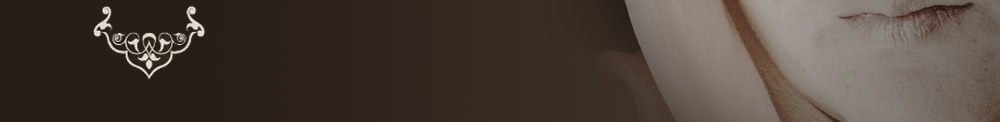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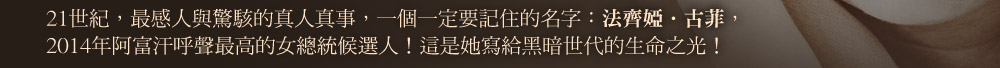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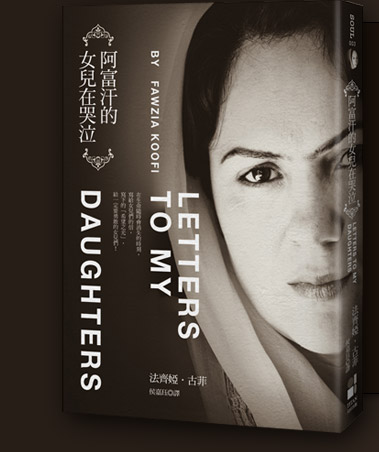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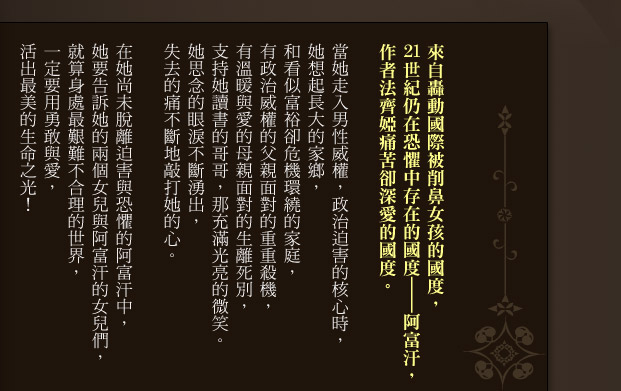
| 法齊婭.古菲 Fawzia Koofi◎著 侯嘉珏◎譯 定價:320元 特價79折:253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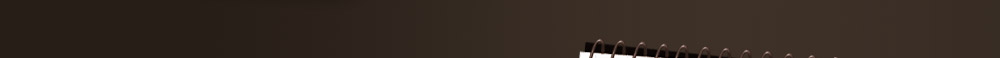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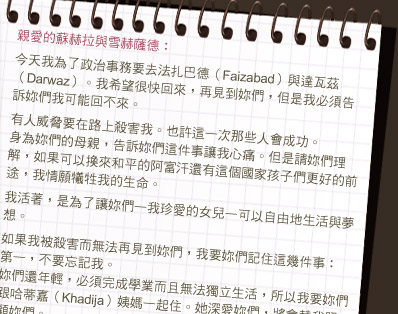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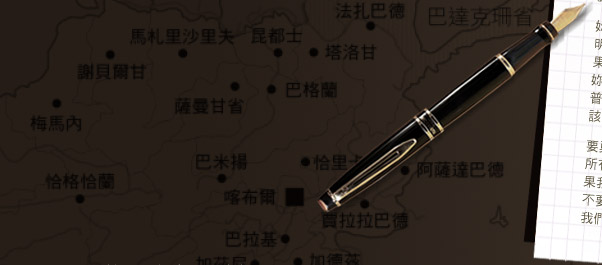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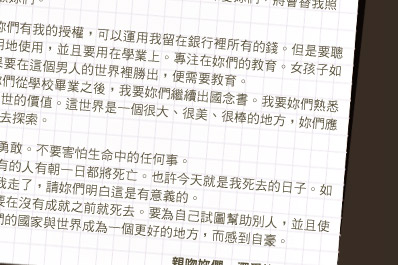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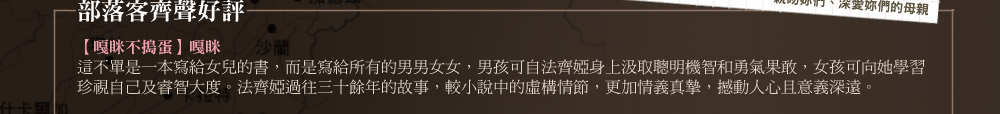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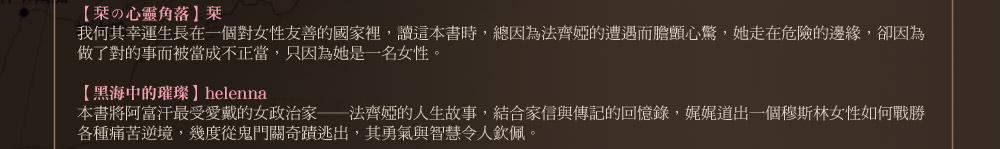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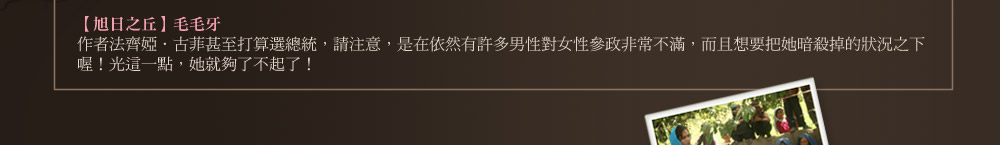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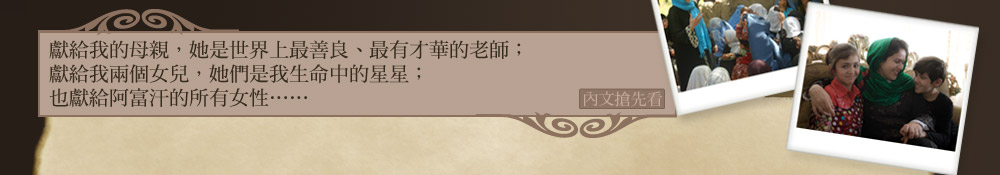

一九七五 我是我父親二十三個孩子中的第十九個,而且是我母親最後一個孩子。我母親是我父親第二位太太。她懷上我的時候,因為已經生下了前面七個小孩而耗盡體力,也因為在我父親最新、最年輕的太太面前失去他的歡心,而憂鬱沮喪。所以她想要我死。 我出生在田地裡。每年夏天,我母親和一隊僕人會旅行到山巔,那裡芳草鮮美,可以放牧我們的牛羊。這是她逃離家裡幾個星期的機會。她掌管全程的運作,蓄積足夠的果乾、堅果、米和油,以供給一小隊旅人離家三個月左右的需求。為這旅程的準備工作和打包功夫十足讓人興奮。在隊伍騎上馬和驢,為了尋找更高的土地而啟程翻山越嶺之前,每一件事都被計畫到最枝微末節的程度。 我母親熱愛這些旅行,她騎馬穿越村子時,對於短暫脫離家裡和家務的桎梏,得以呼吸山中清新的空氣,露出顯而易見的喜悅。 當地流傳著,越有權力與熱情的女人,穿著罩袍騎在馬背上的樣子越好看。我也聽說沒有人在馬背上比我母親美麗。她以獨特的方式支撐她的體態、背脊與尊嚴。 但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一九七五年,她並不快樂。更早的十三個月前,她站在我們那間寬廣、不規則延展的土泥宅(hooli)平房的黃色大門旁,看著迎娶的隊伍從山路蜿蜒而下、穿過村莊。新郎是我母親的丈夫。我父親決定取一個剛滿十四歲的女孩子做他第七位太太。 他每一次再婚,我母親就遭受一次重創—雖然我父親喜歡開玩笑,說每來一位新太太,我母親就變得更加漂亮。在我父親所有的太太中,他最愛被叫做比比將(Bibi jan)(字面譯為「漂亮寶貝」)的我的母親。但是在我父母親的山村文化裡,愛情與婚姻鮮少指同一件事。婚姻是為了家庭、傳統與文化,以及服從所有那些被視為比個人快樂還重要的事情。而愛情是沒有人被期望有所感覺或是有所需求的東西。它只帶來麻煩。人們相信,快樂存在於不帶懷疑地善盡職責之中。而我父親真誠地相信,擁有他這樣身分地位的男人,有責任娶好幾個老婆。 我母親那時安穩地站在土泥宅門後寬大的石頭露臺上。十幾、二十個馬背上的男人緩緩騎下山丘,我父親身穿他最好的一套白色傳統禮服(shalwar kameez)(長外衣與長褲)、棕色腰帶和羊皮小帽。他的白馬身上有明亮的粉紅色、綠色和紅色羊毛流蘇,從裝飾的馬勒上垂吊下來。白馬身旁有好幾隻體型較小的馬,載著全都穿白色罩袍的新娘和她的女性親人,她們陪伴她,到她將與我母親和其他也稱我父親為丈夫的女人們共享的新家。我父親長得矮,眼距很近,蓄著修剪整齊的山羊鬍。他優雅地笑著,和前來迎接他並且觀禮的村民們握手。他們彼此叫喚著:「瓦奇•阿卜杜爾•拉曼(Wakil Abdul Rahman)到了,」以及「瓦奇•阿卜杜爾•拉曼帶著很漂亮的新娘子回家了。」他的民眾愛戴他,所以相當期待。 我的父親瓦奇(議員)•阿卜杜爾•拉曼是阿富汗國會裡的一員。他代表巴達克珊省的人民,就像我現在所做的。在我父親和我成為國會成員之前,我父親的父親阿贊沙(Azamshah)是社區的領袖及部落長老。在我家人記憶所及,當地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一直是我們的傳統與榮耀。可以說,我身體裡流著的政治血液,就像流過巴達克珊省山嶺與河谷的水流那樣強而有力。 巴達克珊省的庫夫區(Koof)和達瓦茲區在十分偏僻的深山裡,我的家族與我的姓氏就來自那裡。即使在今日從首都法扎巴德開車,也會花上三天才到得了。而且那是在天氣好的時候。在冬季,山上的小徑完全封閉。 當然,我祖父不是唯一用這麼落後的方法旅行的人。任何一個村民能夠和比較大的鎮上聯繫的唯一方法,就是騎馬或走路;那是農民買回種子或是帶牲畜到市場的方法,是病人去醫院的方法,也是被婚姻阻隔的家人探望彼此的方法。旅行只在溫暖的春季與夏季的月分裡才有可能辦到,而且即使在那些時期也很危險。 所有的旅程中,最危險的地方,就是阿坦加棧道(Atanga crossing)。阿坦加(Atanga)是阿姆河(Amu Darya River)邊的一座大山。這條清澈的碧綠河道分隔了阿富汗與塔吉克,它有多美,就有多危險。在春天雪融又下雨的時候,河岸潰堤,生出許多致人於死的激湍。阿坦加棧道是一串由粗糙木頭做成、綁在山兩側的階梯,供人爬上山再由另一側爬下山。 木梯很小很滑、搖搖晃晃。只要一小步失足,就會有人直接掉進河裡被捲走,必死無疑。想像一下從法扎巴德帶著剛採買好的貨物回來,也許有一袋七公斤重的米、鹽或是油—那是支撐一家子度過一整個冬天的珍貴物資—而且在走了七天的路之後已經筋疲力盡,然後必須冒著生命危險,越過可能已經造成許多朋友和家人死亡的不牢靠的通道。 我祖父忍受不了年復一年看著他的人民這樣死去,於是他竭盡所能,逼政府建造一條像樣的道路與更安全的棧道。然而,儘管他可能比巴達克珊省大部分的人更富有,他仍然是一個住在偏僻村莊裡的地方官。旅行到法扎巴德是他盡了最大的力氣可以做到的事。但是他沒有方法或是力量旅行到喀布爾(Kabul),那裡是國王和中央政府所在地。 我祖父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改變不會到來,他決定最小的兒子將繼承他的競選角色。我祖父開始打點我父親未來的政治生涯時,我父親還只是個小男孩。幾年後的某一天,在經過好幾個月的紮實遊說之後,我父親在國會裡最大的一次成功之舉,就是實現我祖父在阿坦加通道造路的夢想。 這些早期歲月讓我父親在有關社區的議題上打下堅實基礎,他長大成人之後,已經準備好要領導人民。時機很完美,因為在那個時候,真正的民主才正在阿富汗起步。一九六五年的時候,國王決定建立一個民主的國會,給予人民做決定的權利,允許他們投票選出各地國會成員。 巴達克珊省的人民,認為他們長久以來遭受中央政府的忽視,對於他們的意見終於可以被聽見,感到很興奮。我父親被選為有史以來第一位達瓦茲的國會議員,他代表的是阿富汗裡也是全世界中最貧窮的人民。 我的父親很快地,在國王的國會裡獲得了工作最認真的名聲。雖然巴達克珊省仍然極度貧窮,但是阿富汗整體來說是昌平的日子;國家治安、經濟和社會大致上都很穩定。不過,這不是我們國家的鄰居們願意接受的事。在阿富汗有一個說法,我們的地點與地理位置—位在歐洲、中國、伊朗和俄羅斯的強權之間—對阿富汗不利卻有利於全世界。這是真的。問問任何一個會玩「戰國風雲」(Risk)—玩家目的在占領世界的版圖戰棋遊戲—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你贏得了阿富汗,你就贏得了進入世上其他地方的大門。這說法一直都是正確的。過去在冷戰巔峰時期,我的國家在戰略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早已經形成之後將會降臨到它身上的悲劇命運。 父親在喀布爾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提倡建造道路、醫院與學校,而且成功地獲取資金完成一些計畫,雖然不是全部。在喀布爾的管理者沒有將我們的省看得特別重要,所以他很難獲得中央的資金。這件事經常使他生氣。 我母親記得她如何在每年國會休會之前一個月,為我父親的返家做準備。她為他準備各式各樣的蜜餞和果乾、打掃房子、派僕人到山上採集木頭,準備好他回家之後所有烹煮的需求。傍晚時分,一路載運著木材的長長驢子隊伍會進到土泥宅大門內,而我母親會指揮他們進到園子角落的柴房。她以自己的方式像我父親一樣,努力地工作,凡事只求最好,從不接受次等的,總是追求盡善盡美。但是我父親很少感謝她所做的。他在家裡是個令人害怕的暴君;我母親身上的瘀傷就是證明。 我父親與七位太太的婚姻中有六件都是政治婚姻。他藉由和鄰近部落的領袖或強而有力的長老最鍾愛的女兒結婚的戰略,鞏固與保全他自己當地王國的權力。我母親的父親就是曾與我父親村子有過爭鬥的相鄰行政區裡一位重要長老。他透過娶我母親,實質地取得了一份和平條約。 他的太太中,少數幾個是他愛過的;兩個是他離婚過的;大部分是他忽視的。他一生中總共娶了七位太太。我母親無疑是他最鍾愛的一個。她嬌小,有漂亮的鵝蛋臉、蒼白的皮膚、棕色的大眼、黑亮的長髮和齊整的眉毛。 僕人們和我哥哥們會排成一列,將滾燙的鍋子從廚房傳遞到隔壁我父親娛樂客人的賓客室。女人不准進入這些男人獨有的區域。在我們的文化中,結了婚的女人不應該被非她親戚的男人看見,所以在這些場合中,從來不被期待做家事的我的哥哥們,就必須幫忙。 在這樣的晚宴中,我父親要求所有事情都要完美。米飯必須鬆軟,而每一粒米都必須完美地分開。如果符合他的標準,他會為他的財富和所選出的最傑出的太太,滿意地微笑。如果他發現有幾顆米粒黏在一起,他的臉色會變得難看,然後他會禮貌地向賓客們告退、走進廚房,不發一語地抓住我母親的頭髮、扭過她手中的金屬勺子往她頭上打。她的手—已經滿是傷疤而且變形—會抱住頭保護自己。有的時候,她被打到不省人事,卻會再度醒來。她不顧僕人們驚恐的目光,往頭皮上抹灰止血,然後再度執掌,確保在下一批米中,米粒完美地分開。 她決心實現我父親的想法,不僅僅是因為責任感或是恐懼,也因為出於愛。她真心又全意地愛慕他。 所以第七位太太進門的那一天,我母親是心懷悲傷看著迎娶隊伍蜿蜒穿過村子。她在露臺上,站在一個正拿杵在石缽裡舂麵粉的女僕身邊。我母親強忍住淚水,抓過舂杵猛力往石缽裡搗,雖然身為當家女主人的她平日裡不會做這些工作。 而現在,十三個月過去了,我母親在偏遠的山區陋室裡生下我。失去她心愛男人的歡心,她孤獨又不幸。三個月之前,年輕太太才剛生下一名臉色紅撲撲的活潑男寶寶,名叫恩那亞特(Ennayat)。他的眼睛大得像巧克力碟子。我母親不想再有孩子,她知道這是她最後一次生產。整個懷孕過程中,她虛弱、蒼白,而且體力匱乏,她的身體因為已經生過好幾個小孩,已經山窮水盡。而恩那亞特的母親卻比以往更加美麗,因為初次懷孕的喜悅,而容光煥發、乳房堅挺、雙頰緋紅。 我母親在她自己懷孕六個月時,接生恩那亞特到人世間。他肺部因為第一次呼吸而脹滿,哇哇大哭著來到世上。比比將(Bibi jan)雙手摸著肚子,無聲地祈禱她自己也會生下一個男孩兒,這樣她就會有機會贏回我父親的偏愛。在我們村裡的文化中,女孩子被認為沒有價值。即使在今日,女人也祈禱生下男孩,因為男孩給予她們地位,而且讓她們的丈夫高興。 我母親在產下我的過程中,因為陣痛而扭滾了三十個小時;在我出生時,她已經是半昏迷狀態,只勉強有力氣在知道我是個女孩時,表達失望氣餒。我被抱給她看時,她轉過身,拒絕抱我。我膚色斑駁,長得很小—和健壯的恩那亞特不相像得無以復加。我母親在生下我後瀕臨死亡。沒有人在乎這個剛生下的女孩是死是活,所以她們忙著救活我母親的時候,我被包裹在棉布襁褓巾裡,放在外頭曬太陽。 我就在那裡躺了一天,小小的肺都快被我哭出來。但是沒有人前來。她們滿心想順其自然,讓我自生自滅。我的小臉被太陽嚴重曬傷,甚至在我青春期的時候,臉上還帶著當時的疤。 到她們可憐我,將我帶進屋裡時,我母親已經好很多。她對於我活了下來感到很驚奇,並且被我臉部曬傷的程度嚇了一跳,驚恐地倒抽一口氣,起初的冷漠融化成母性的本能。她將我放在懷裡抱著。當我最後停止哭泣時,她卻開始靜靜地啜泣,暗自下定決心,不再讓我受任何傷害。她明白真主為了某種原因,要我活下來,以及她應該要愛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為什麼要饒過我。或是為什麼要在那之後好幾次我可能會死去的時機饒過我。但是我知道祂對於我,有祂的旨意。我也知道從那一刻起,祂真的護佑我,讓我成為比比將最寵愛的小孩,形成母女之間永不可破的情誼。 親愛的蘇赫拉與雪赫薩德: 在我生命的初期,我學到了當一個阿富汗的女孩有多麼的困難。一個新生女孩經常聽到的頭幾個字,就是對於她母親的憐憫。「只是個女孩,可憐的女孩兒。」那可不是什麼對於來到世間的歡迎。 之後,當女孩兒長到了讀書的年紀,她不知道會不會獲准上學。她的家裡是不是勇敢或是富有到送她上學?當她的兄弟長大的時候,會代表這個家,他的薪水會拿來養家,所以每個人都想要男孩受教育,而女孩們在我們的社會裡,唯一的未來通常只有婚姻。她們對家裡沒有財務貢獻,於是在許多人的眼裡,教育她們沒有什麼用。 如果家人不理會這些風涼話,讓女孩長到十六歲,在為她找到伴侶之前,他們允許她依照自己的選擇婚配,或是至少允許她與父母的選擇意見不同,那麼她就有機會體驗人生中的一些快樂。然而,如果家裡處於財務壓力下,或是受到閒話的影響,他們會在女兒十五歲之前將她嫁出去。在一出生時就聽見「只是個女孩」的小女生,將會成為母親;如果她生下一個女孩子,她的寶寶將聽見的頭幾個字也會是「只是個女孩。」而這會一代一代的流傳下來。 我就是這樣開始的。由一個不識字的女人所生,「只是個女孩」。 深愛妳們的母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