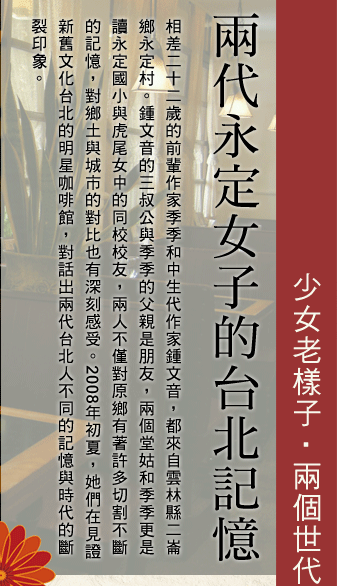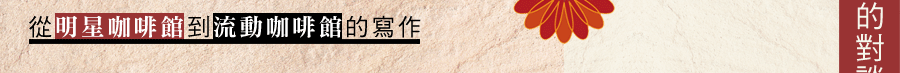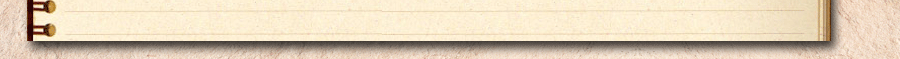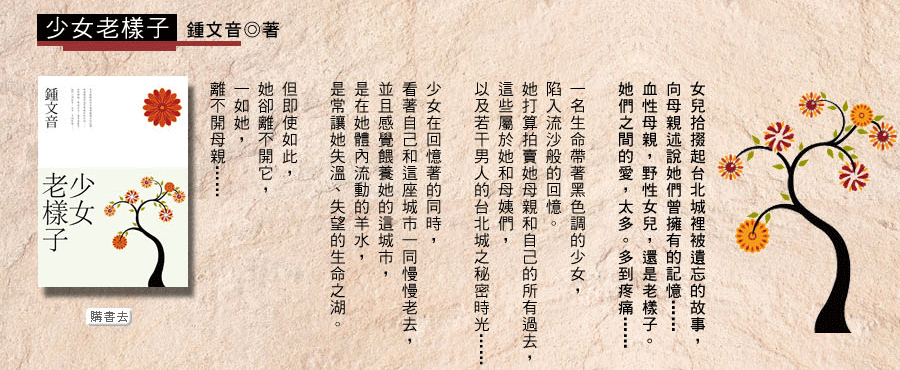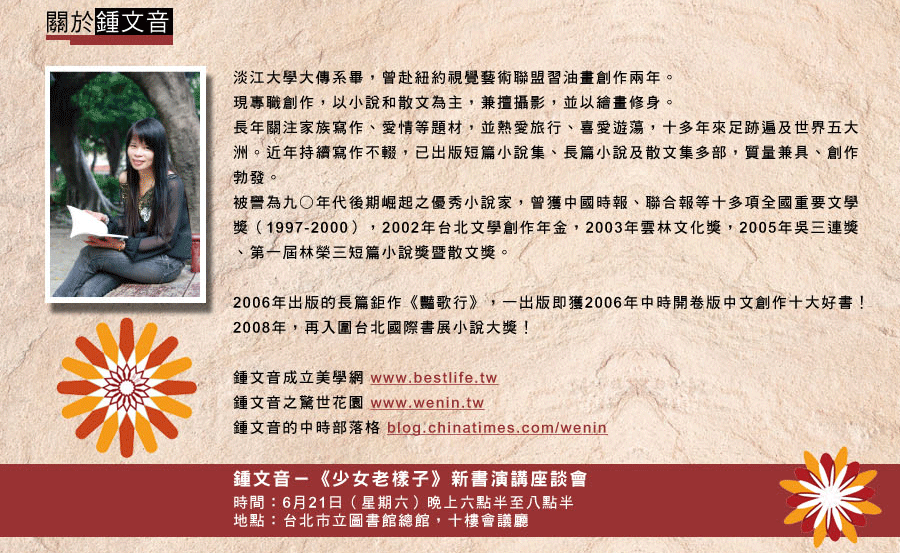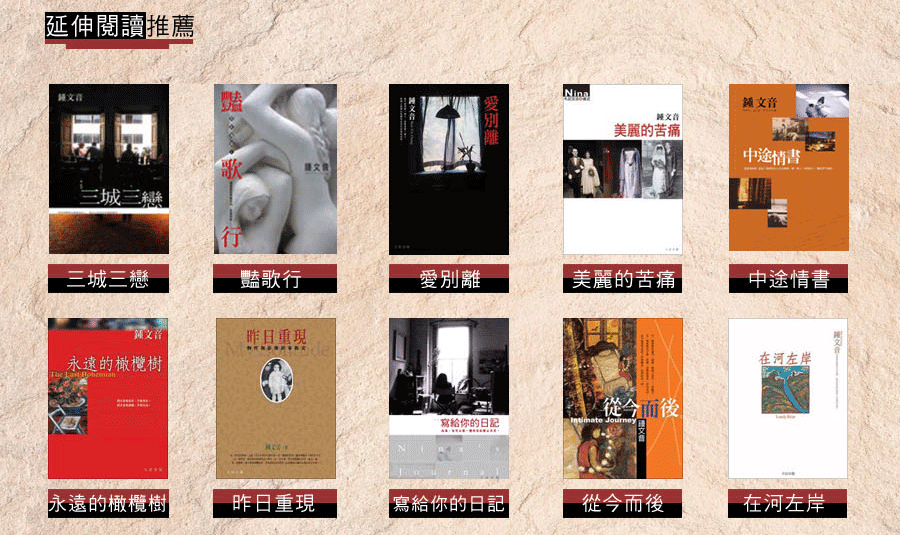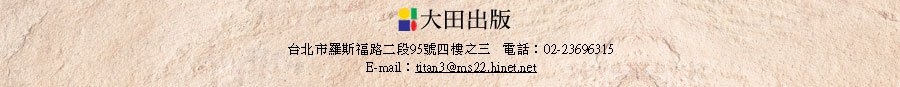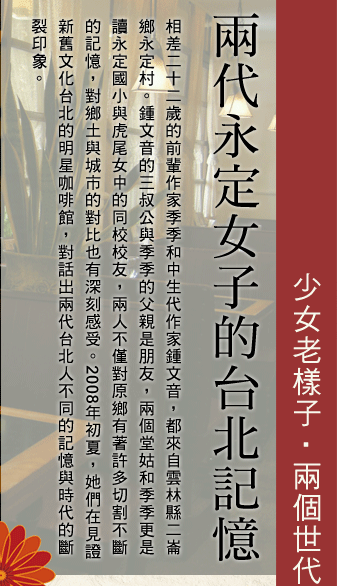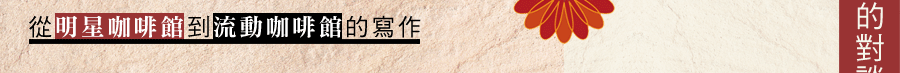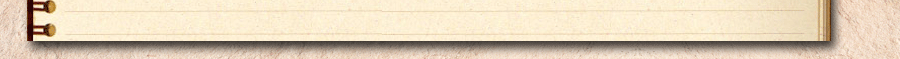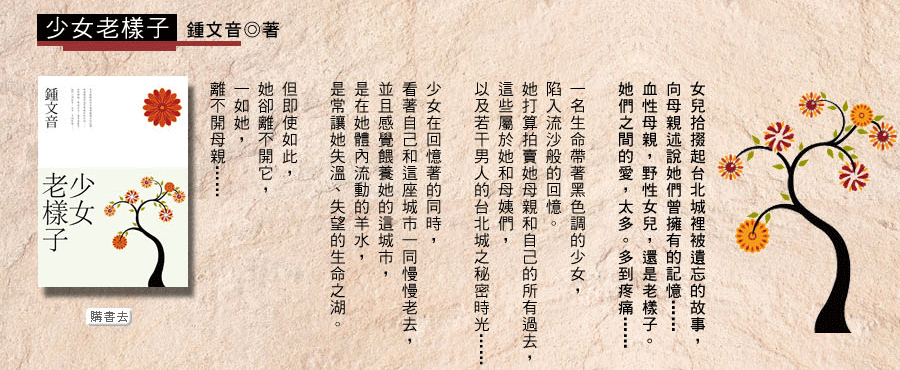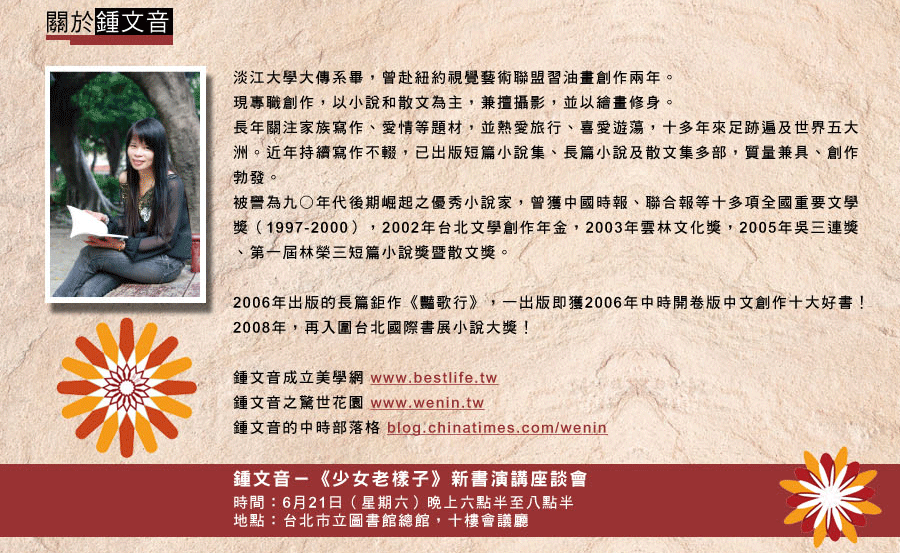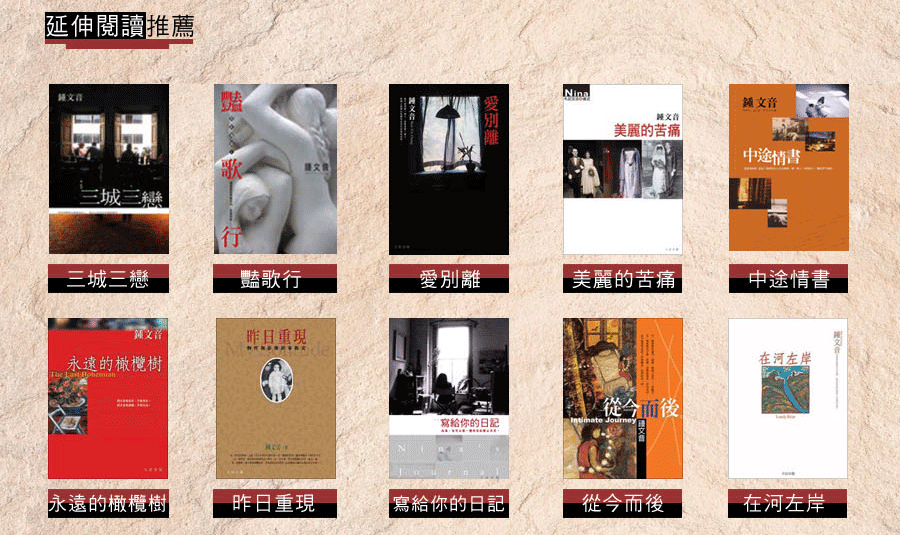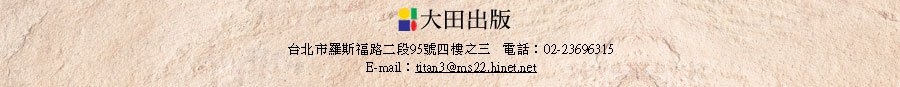季季:
我那一代,台北能去的咖啡館不多。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衡陽路上文星書店斜對面的田園咖啡館,年輕人愛去那裡談情說愛,另外是長安東路上的月光咖啡館,那裡的古典音樂很棒。
明星咖啡館,常到訪的是作家和藝術家。最早到明星咖啡館的作家,大概是白先勇、王文興、 陳若曦、王禎和他們《現代文學》那一批。一九六四年我來明星寫作時,他們不是出國就是去當兵,已經不在明星出入了,通常是我一個人在三樓寫稿。到了一九六四年秋天,考上政大的林懷民,也會在周六周日到明星來寫作,林懷民寫一寫,還會拿來問我:喂,妳看我這段寫得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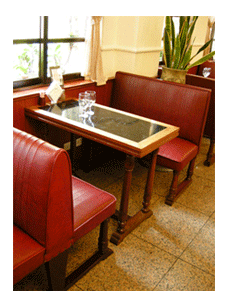 鍾文音: 鍾文音:
季季對年代清楚得嚇人,像我記事情依賴的都不是年代,甚且我對時間與年代常有模糊的錯置感。我寫東西依據的是「畫面」,殘存在我心中的「影像」。
同時,我們這一代也沒有文壇結盟,雖然同輩寫作者也都認識,偶爾也有聚會。但卻沒有內在心情的掛勾,頂多在一起就閒聊些流言,對於彼此真實生活面貌卻包了層保護膜,不參與他人內心世界,也不準備打開內心世界給別人看(所以自殺的作家都是屬我這一輩的),當然也沒有人會問彼此寫的怎麼樣了,關心的都是很淺的東西。
表面看起來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切都很公開,什麼消息都會不逕而走,但其實我們彼此十分陌生,像我總是習慣隱藏,別人看到公共場合的我未必是「真我」,「真我」其實都在寫作裡。
我不知別人如何,但我是絕對沒有團體的人,我在團體裡會和善簡單,因為我把一些黑暗躲藏起來。說來,我這一代確實是生活在繁華城市的流動孤島。至少這麼多年我都是這樣。
季季:
對我們永定人而言,初來台北其實是異鄉人。不過我們那一代和寫作同好的來往比較密切,生活中各種的沒有,就可能有各種的有。沒有電話、沒有手機,就寫信,或親自登門拜訪。在家寫稿,有時門被敲響,原來是編輯、作家朋友或讀者來訪了。
現在的作家可能不斷的出入各種場域,但沒辦法進入彼此的內心。我們是場域不多,但很快都能進入彼此的內心,知道他們的故事。那時台北沒有所謂的東區,我們常出入的場域,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新公園對面的天琴西餐廳,中山北路上的幾間畫廊。去都是為了朋友的展覽,或見見朋友。那時也沒有兩廳院,聽音樂會都在中山堂與信義路的國際學舍(現已拆除)。
這一代的作家,跟人比較疏離,大概很多是從「我」的內心開始寫作,但我那一代作家是從他者的觀察開始創作的。
鍾文音:
我們兩代寫人物的不同在於,你們有種人事氛圍的情蘊,而我們大多是傾向自剖;你們是有根的記憶,我們看似熱鬧其實孤寂。我們是薄膜下包覆的個體,隔絕整個時代背景,因此寫的都是「個我」的故事,少有他者的故事,也不太去介入他人的生活,至少我是這樣,我覺得我創作,但絲毫沒有文壇之感。另外,我覺得兩代作家的養成方式也不同,你們那一代多是在一群人所主辦的文學雜誌裡發表作品,我們這一代多由文學獎得到名聲,是個我去爭取來的,完全沒有所謂的「前輩」在背後撐著。也很少有「前」人給我鼓勵,我的鼓勵反而都來自很年輕的讀者,她們總是告訴我,我雖然寫的是自己,卻反映了她們的內心。但那些讀者都是陌生人,不像你的年代有來往密切的文壇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