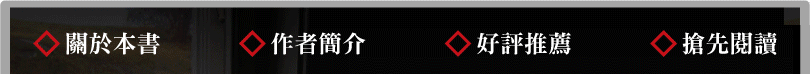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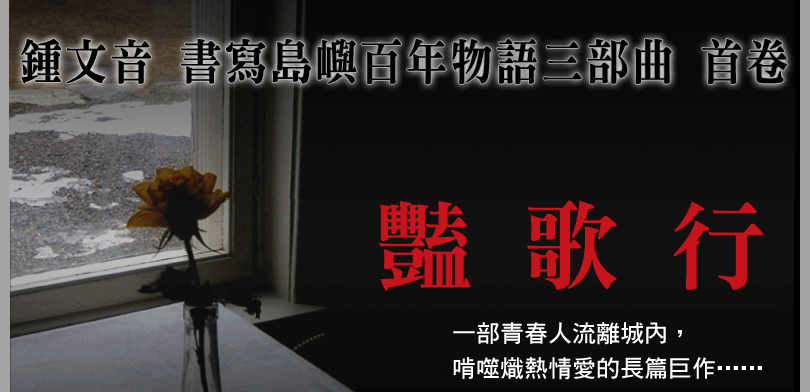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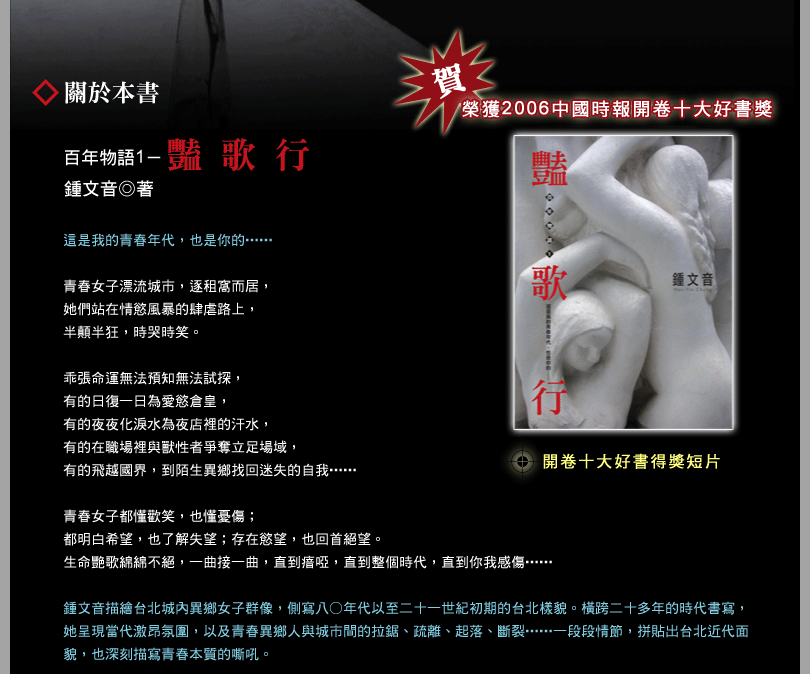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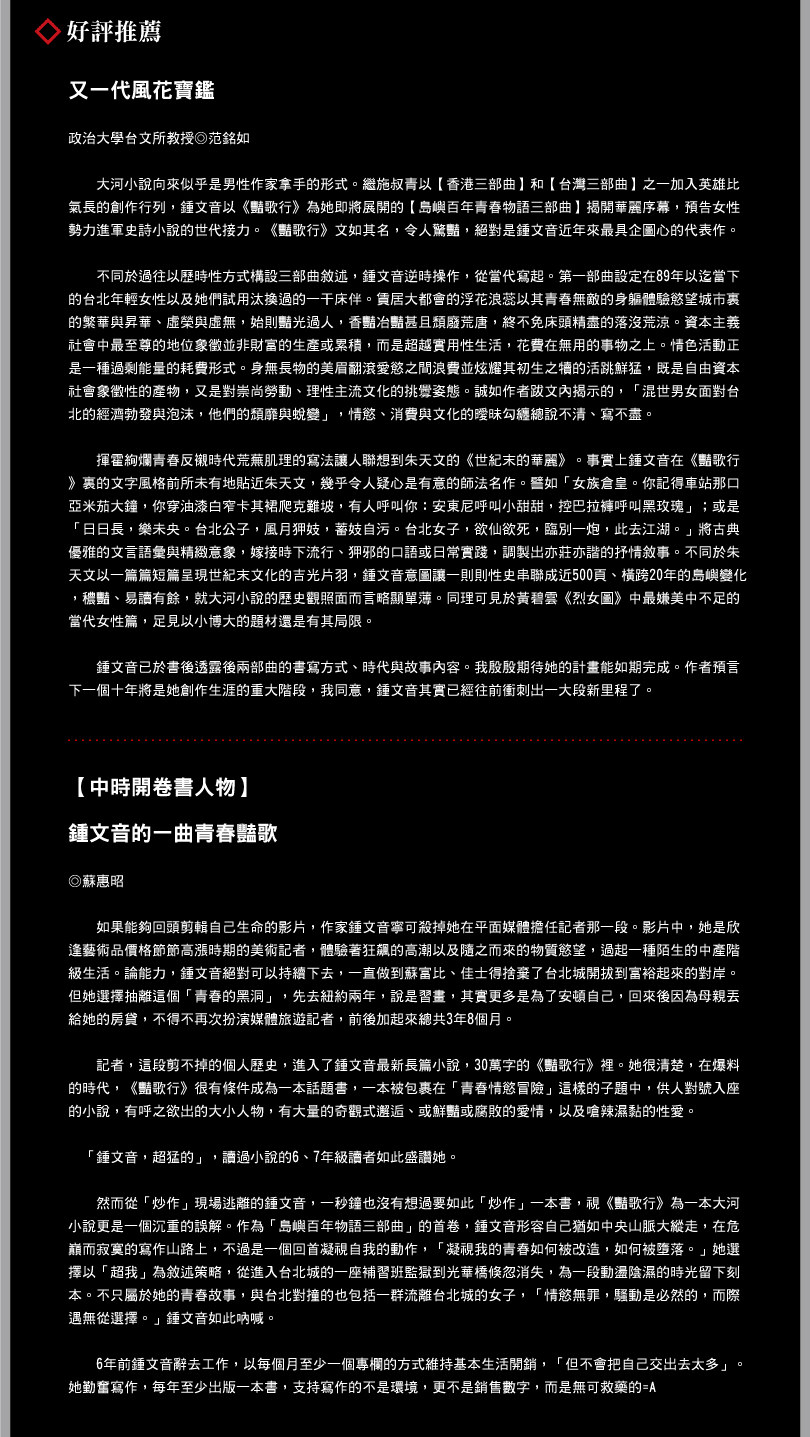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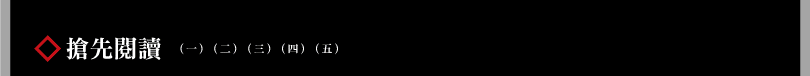
這些年暮冬,雨水出奇得多,日夜溫差形成的霧靄也深,前方城內的樓房燈火全被霧吞歿了。 在無光之城。 你情非得已。 這座城市帶著一種隨興的自我欺騙,不同的人混在一起,就盪出不同的情緒與氣味。你每天都在發現它一些些, 你述寫的大約和自己有關,這也是你的中心軸。在這個軸上所外延出去的現象,能被述說下來,你全憑記憶的隨 儲先生說他本該姓初,他老爹來台灣時發音不清楚又不識字導致他們後代全姓錯了。殷先生說他本該姓應,劇情 你的外省第二代男人在隨著探親返鄉見到新建的祖墳時才了然自己一直都跟錯了姓。你一個朋友,他只用民國年 那年代,住在租窩公社的你們很流行用的家具是懶骨頭。你們生命最大的逸樂也不過是把自己懶成一根骨頭,戀 那時有粗魯的太太會打電話問著你:「我老公在你家嗎?」參加聚會有帶著一張撲克牌的臉指著你說:「你坐到 你們剛剛被流行的詞彙「單身公害」所害。 那時這座城市還沒有長出肺來,大安公園還是「愛情萬歲」裡蔡明亮鏡頭下的泥土荒蕪。 有人記憶國際學舍、眷村,你記得附近的狗園和一家汽車旅館。(幾年後,當你為音樂朋友站上流浪者之歌的舞 經過一些事,一些流離失所,溺水失溫的生命如何能再燃起沸點?一旦生命河道轉向,那麼所有的往昔所造都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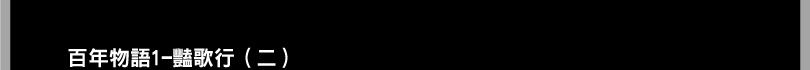
是再也沒有人問你們向左靠還是向右靠,你們只說「我靠」! 整座舊城喧囂著掩藏不住的新城氣息,在圓環立正站好的偉人銅像一一移除,股票持續看漲。(泡沫經濟名詞還 感情一向無法匯兌現金,然現金可以買闊別的親情。讀書尾聲,兩岸開放探親,大你甚多歲的情人們都陸續返鄉 你記得那些年他們總是出出入入海峽兩岸(傳奇盛況不下今日台商,眼淚也搶先在二奶和大陸妹攻陷前幾年已先 那些藥比地理空間還讓你更具異國情調想像,白鳳丸裹在很硬的白色膠殼,切開有二十幾粒豬肝色小米粒丸。你 有的男人說如果可以他一定為你帶隻北京烤鴨或者山東饅頭回來。然而他們帶回來的是兵馬俑、唐三彩、景德瓷 唯一帶給你可供憑弔這段兩岸開放紀念物的卻是你阿母陪你阿姨回上校姨丈老家後,你阿母帶給你的一只玉環, 那時你也還未開始一個人旅行,最遠到吉貝島,踏在島上延伸如靴的海岸線時,你當時以為那就是你的鄉愁盡頭 靠左或靠右? 八○年代第一個離開島嶼的男人寫信給你說,他在戲院前遇見一個大陸高幹美麗女子,後來在看戲時心裡浮起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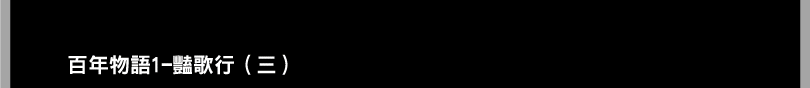
外省掛男人返鄉帶回他們的故事給當時還沒踏上那塊土地的你聽,他們說起那些擋不住的鄉愁,言說那些淚水, 放銃?不解。他解釋那是一種慶典儀式,放銃和放鞭炮意義一般,因為當時還不准放鞭炮。其亡父之弟指著一塊 其中有個男人的父親曾在郵局工作,他不是綠衣人,他是負責拆信的情治員。那些年從家鄉輾轉流徙他地寄到島 他說他喜歡你,因為你散發著吉普賽流浪氣息,這符合男人對於他父親一生遷徙身世的想像。 你睜著你那目珠凹深的黑眼覷他(邊想起母親說的深目無情),聽著笑著,又開始習慣性地在不知要回什麼話時 你想念那些曾經在你生命裡興風作浪的某些老男人(當時他們其實不過處於你現今的三少四壯而已,很快地你將 青春是塑膠做的可熔物質,未建立自我的你,情人欲你成為什麼就形塑成什麼。他要去廣場拍革命學運的照片, 青春人,世界是可塑的。 被時間堆倒的瓦礫下,拾獲的是延展如金的記憶。甜膩沙啞,不矛盾的異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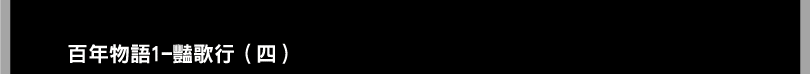
有時候是青春的你們把邂逅的冒險性勾招至際遇裡的,即使這邂逅包含某種污穢的有意偷襲。 然而若不是緣於自我願意的靠近而是來自他者偽善的勾搭,這卻讓你難釋懷。那些年是最易遇到這類不開心的事 在西區青年會幾次游泳的經驗到現在都還清晰聞到那股充滿氯氣的水池黃昏,未下班之際只有幾個像是提早退休 疼惜的猥褻。你創的青春新詞。 怪的是,你也沒有斥怒或者去表明些什麼道德之詞,你抹去滿臉的水,還說了聲謝謝,聲音小小地對陌生的歐吉 有時他們又跟著游過來,並抓起你的雙手說:我們再游幾圈吧。這時你只好訕訕地說想回家了,拋下那些歐吉桑 抱著一袋濕沈沈的游泳衣離開泳池,忽像一片葉子,飄進台北西區的夏日車潮,濃豔的落日逐漸鑲進前方西區百 你感到水中的游泳衣在袋內加溫,發出濕邪,冒著像魚鰓的泡沫。總是像是雨欲至而未至的悶熱盆地,你走著路 城市聲音攪拌耳旁,你與音牆之間只有寂靜和兩腿牛仔褲摩擦的簌響。 十字路口路邊各停一輛馬達聲奇大的發財車,滿滿的西瓜成堆,鳳梨成籃,卡車內的小燈泡在雨絲中搖晃,對半 黑田裡竄出一大群飛蟻,飛蟻不斷地撞著路燈燈火,四散飛蟻撞斷了燈光的續性。焦糖黃翅膀和燈火雲湧成一團 只有亡命飛蟻在狂亂起舞後全定住不動了。大街上飛蛾的斷翅死屍飛飛飛,飄飄飄。 「要變天了,看這些蟻都在尋死呢,活不過今晚啊。」歐巴桑路人經過你身旁時如此地說著。 婦人不經意的語言卻恍然理解了年輕女子的潮騷。性與死亡的雙重奏,使你在這草莽城市度過了騷動歲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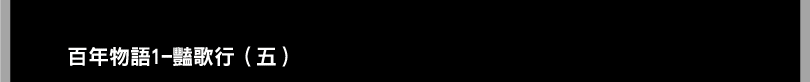
那時你在小村,寂靜午後,影子長長,你總是專心地聽著騷蟬知了從宅院後溢出的音譜。 在那廣大寂寥的音譜世界裡,有時會有個聲音喚你。 他要你過去,一個吻,一張圖。你說你自己也會畫圖,學校教室壁報貼滿你的畫。他說他的圖不一樣,以後可以 那是鄰近某戶的畫家,髒髒黑黑的,但笑起來印象裡頗為善意。善意也許是孩童目光無知所造成的灰灰印象又或 畢竟六歲離此刻台北城的你是那麼遙遠。 後來你遇上無數個和你六歲時遇見的老畫家差不多的潦倒人生。 他們的潦倒不是真的潦倒,是因為自傲裡的不屑,或者極端的是∣∣潔癖清高後所導致的潦倒,酗酒封閉,憤世 你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可以如此不屑,但你又看見他們其實內心是渴望的,他們看不見他們的愛慾不斷長出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