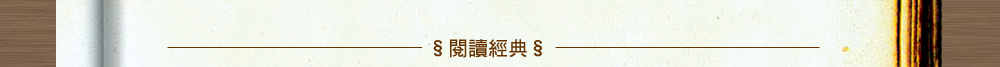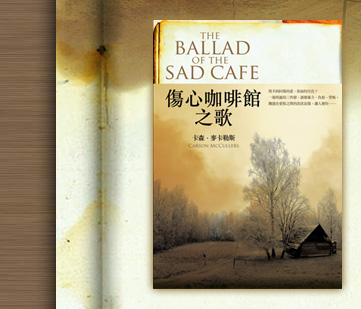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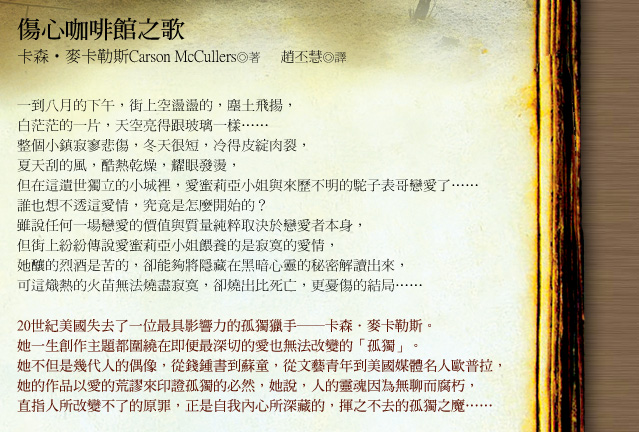
| 定價:220元 特價:174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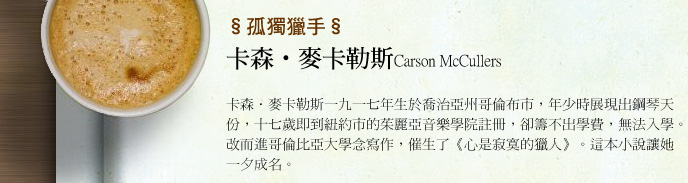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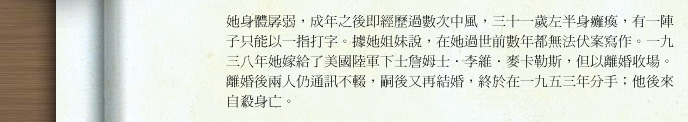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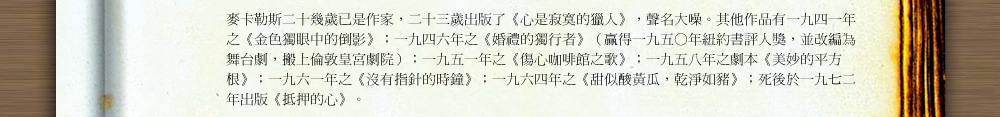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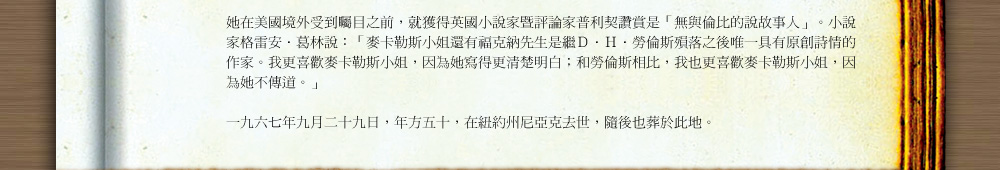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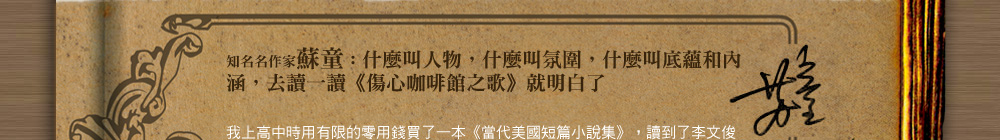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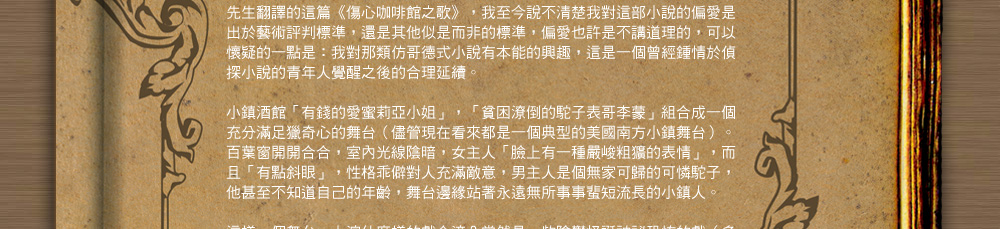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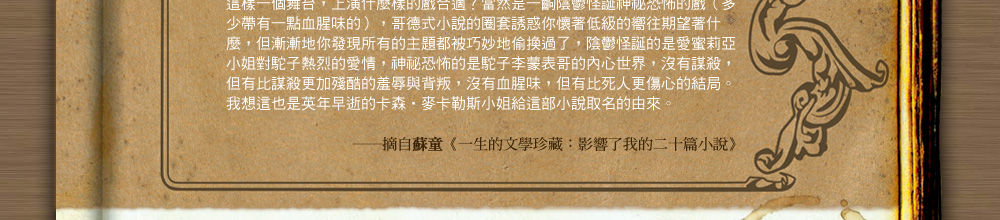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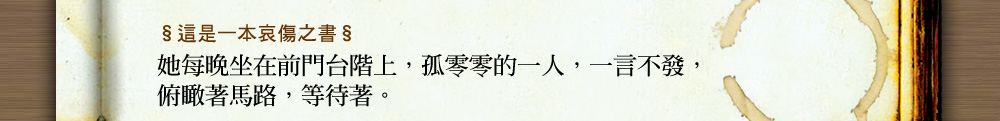

小城冷冷清清的,實在沒什麼看頭;唯有一家紡織廠,一些僅有兩房的屋宇供勞工住宿,幾棵桃樹,一座有雙色窗的教堂,還有一條人車稀少的大街,說是大街可是只有一百碼長。到了週六,附近農場的佃農會進城來交易聊天,除此之外,整個小城寂寥悲傷得很,像是窮鄉僻壤,和世上的其他地方都隔絕了音訊。最近的火車站在社會市,灰狗巴士和白巴士也只行駛三哩外的佛克斯瀑布路。這裡的冬天雖短,卻是冷冽砭骨,夏天則酷熱難當。 若你在八月某天下午走在大街上,根本無事可做。最大的建築在小城正中央,整棟都用木板給釘死了,屋子向右偏斜得厲害,看起來隨時都會倒塌。這棟屋子很舊了,總莫名其妙透著一種破裂的感覺,讓人摸不透是怎麼回事,猛然間會發現房子前廊的右側曾在許久許久之前粉刷過,部分的牆壁也是——不過油漆沒刷完,所以屋子分成了兩半,一半比較陰暗骯髒。這棟屋子一絲人氣也沒有。倒是二樓有一扇窗沒用木板釘死;到了近黃昏的時間,那時的天氣最熱,會有一隻手緩緩推開窗板,一張臉會俯視小城。那張臉就像是夢中常見的恐怖朦朧的臉孔——性別不明、慘白白的,兩隻灰色交叉的眼睛,鬥雞似的,像是在交換什麼祕密又冗長的哀悽眼神。這張臉孔會在窗前流連個一小時左右,接著窗板又一次關上,而通常大街上也是一個人影都沒有。這些個八月的午後——等你值完了班,真的是無所事事;乾脆走到佛克斯瀑布路去聽那些鎖在一塊服外役的犯人腳上的鐵鍊鏘鎯響算了。 不過可別小看了這個地方,在這座小城裡曾經開過一家咖啡館。而這座用木板釘死的老屋子曾有過的繁華也不是方圓數哩之內的任何地方比得上的。這裡曾有覆著桌布、擺著餐巾的餐桌,五彩繽紛的彩帶隨著電扇向四方飄送,週六晚上高朋滿座。咖啡館的主人是愛蜜莉亞.伊文斯小姐,但是讓這地方生意興隆的人卻是一個駝子,叫做李蒙表哥。另一個在咖啡館故事裡也參了一腳的人是愛蜜莉亞小姐的前夫,他是個壞胚子,在監獄關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回到小城,興風作浪,大肆破壞,隨後又拍拍屁股上路了。從此之後,咖啡館就歇業了,但是大家仍念念不忘。 咖啡館之前並不是咖啡館。愛蜜莉亞小姐從她父親那兒繼承了這棟屋子,原本是一家商店,主要販賣飼料、鳥糞石、民生必需品,諸如粗粉和鼻煙。愛蜜莉亞小姐很富有。除了這家雜貨店之外,她還在小城後頭三哩的沼澤區裡弄了個蒸餾酒坊,出產本郡最上等的烈酒。她這個女人的皮膚黑,身材高,骨骼和肌肉像男人,頭髮剪得短短的,向後梳,露出額頭,而她日曬的臉龐有一種緊繃的、憔悴的特質。要不是她微微有些鬥雞眼的話,當年的她是可以算得上標致的。有不少人想追求她,但是愛蜜莉亞小姐不稀罕男人的情愛,始終是孤家寡人一個。她的婚姻也跟本郡其他人的婚姻都不同——那是一場離奇的、危險的婚姻,只維持了十天,震驚了整個小城,人人都猜不透原因。除了這一次詭異的婚姻之外,愛蜜莉亞小姐一直都獨居。她經常躲在沼澤區的小棚子裡好幾個晚上,穿著工作服和橡膠長靴,默默的看著蒸餾房的火。 愛蜜莉亞小姐就是這麼靠著一雙手致富的。她在附近的小鎮販賣小腸和香腸。秋天天氣好的時節,她研磨高樑,而她桶子裡的糖漿是暗金色的,甜香味美。她只花了短短兩週的時間就在她家店鋪後頭蓋了一間磚廁所,而且她的木工手藝也十分高明。愛蜜莉亞小姐最不拿手的一件事就是和人打交道,除非是隨性所至或是重病在身的人,否則人這種東西是不能放到手上,一夕之間轉變成有利潤的東西的。所以一般人對愛蜜莉亞小姐唯一的功用就是可以讓她從他們那兒賺到錢,而且她在這方面相當的成功。以農作物和地產抵押放債,一間鋸木廠、銀行的存款——方圓幾哩之內沒有人比她更富有。要不是她唯一僅有的小缺點,也就是她對法律訴訟及上法庭的癮頭,她甚至可以是一位富有的國會議員。她可以為了一樁芝麻綠豆大的小事纏訟許久。據說愛蜜莉亞小姐就算是走在馬路上被石頭給絆了一下,她都會立刻東張西望,看有沒有什麼可以讓她告上法庭的。撇開這些法律訴訟不談,她的生活平靜無波,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差不多。除了那一場為期十天的婚姻之外,她的生活都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愛蜜莉亞小姐三十歲的那年春天,事情不一樣了。 那是四月裡一個寧靜的晚上,將近午夜時分,天空是藍色沼澤的虹彩色,月兒又清楚又透亮。田裡的莊稼欣欣向榮,幾週來紡織廠晚上也忙個不停。小溪下游那間方形的磚製工廠亮著黃澄澄的燈光,模糊的織布聲不斷地響著。這樣的夜晚最適合聽見在漆黑農田的另一邊,某個黑鬼緩緩哼著歌,準備要去跟情人幽會。不然一個人靜靜坐著,撥弄吉他也不錯,再不獨自一個人休息,什麼也不想也是一宗樂事。那晚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可是愛蜜莉亞小姐的雜貨鋪卻點著燈,門廊上還站了五個人,其中之一是史當皮.麥克菲,他是個工頭,長了一張紅臉,一雙手卻很嬌小,泛著紫色。站在門廊最上層階梯上的是兩個男孩,雷尼家的雙胞胎,兩個都瘦瘦長長的,反應遲鈍,白色頭髮,綠眼惺忪。再一個人是亨利.梅西,他是個害臊膽怯的人,溫吞吞的個性,還喜歡窮緊張,坐在最底層的階梯上。愛蜜莉亞小姐自己則倚著敞開的門,雙腿交叉,腳上蹬著一雙大沼澤靴,很有耐性地解開一根她隨手拾到的繩子。五人有很長一陣子都沒開口。 雙胞胎中的一個拿著啤酒,看著空盪的街道,第一個出聲。「我看見有東西朝這兒來了。」他說。 路上的形影仍然太遠,無法辨識。月亮把路旁開花的桃樹照得陰影扭曲,空氣中有桃花和春草的甜香,混合了附近沼澤烘烘暖的酸味。 「不對,是哪家的小鬼頭。」史當皮.麥克菲說。 愛蜜莉亞小姐默默盯著馬路,已經放下了繩子,用褐色見骨的手撫弄著工作服的帶子。她皺著眉頭,一綹黑髮落在額頭上。眾人正屏息以待,某家養的狗狂吠了起來,一直吠到某人大吼,制止了牠。他們直等到路上的形影進入了門廊黃光的範圍,才看清楚來者是什麼。 那是個生人,這種深更半夜的時候有個生人徒步走進小城可是很稀罕的事情。再者,那人還是個駝子,大概只有四呎多一點點,他的大衣破爛褪色,只遮到膝蓋。兩條彎曲細瘦的腿似乎撐不住歪扭的大胸膛以及兩肩上的腫塊。他的頭非常大,兩眼凹陷,眼珠是藍色的,嘴巴倒是又小又輪廓分明。那張臉孔同時給人溫和又無禮的感覺——眼前他蒼白的皮膚被塵土給弄成了黃色,眼睛下方還有兩圈淡紫色的眼圈。他提著一邊重一邊輕的舊手提箱,是用繩子綁住的。 「晚安。」駝子說,聽得出上氣不接下氣。 愛蜜莉亞小姐聆聽他解釋,腦袋偏向一邊。她一個人吃週日晚餐,她的房子從來沒有被一票親戚給擠滿過,而且也從來不跟別人沾親帶故。她在奇霍是有個姨婆擁有一家出租馬廄,可是那位姨婆也過世了。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一等親住在二十哩外的城鎮,但是這個表親和愛蜜莉亞小姐處得不好,若是偶然在路上碰見,他們都會朝路邊吐口水。不時會有人使盡了心機想跟愛蜜莉亞小姐攀親戚,不過沒有一個人得逞。 駝子開始拉拉雜雜的長篇大論,提起一堆的姓名地名,門廊上的聽眾聽的是一頭霧水,覺得跟眼前的主題好像搭不上邊。「所以芬妮和瑪莎.基瑟普是同父異母的姐妹,而我是芬妮第三個丈夫的兒子。這麼一來,妳跟我就是——」他彎腰,動手解開行李箱。他的手就像是骯髒的鳥爪,還抖個不停。箱子裡裝滿了各式各樣的垃圾——破爛的衣服,怪模怪樣的廢物,像是從縫紉機上拆下來的零件,反正就是壓根沒用的玩意就對了。駝子在這些東西裡翻來找去,掏出了一張舊照片。「這是我媽和她妹妹的照片。」 愛蜜莉亞小姐一聲不吭,只是慢吞吞的左右扭動著下巴,從她的臉色你也知道她腦子裡轉著什麼念頭。史當皮.麥克菲把照片拿過來,移向光源。照片上是兩個蒼白弱小的小孩,一個兩歲,一個三歲左右。但是臉孔只是模糊的兩團白,隨便哪一家的相簿都能找出這麼一張相片來。 史當皮.麥克菲把照片還給他,並沒有多嘴。「你是打哪兒來的?」他只這麼問。 愛蜜莉亞小姐仍是一聲不吭,兀自倚著門框,俯視著駝子。亨利.梅西緊張兮兮的眨眼睛,揉搓著手,沒多久就靜悄悄從最底層階梯離開,消失了蹤影。他是個好人,駝子的處境打動了他的心,所以他不想留下來看愛蜜莉亞小姐把這個外來客趕出她的產業,驅逐出小城。駝子站在階梯底,行李箱打開來;他吸吸鼻子,嘴唇顫抖。或許是他也感覺到自己騎虎難下,也許他是明白了提著一箱的垃圾闖入一座陌生的小城,還聲稱是愛蜜莉亞小姐的親戚是一件多可悲的事。無論是哪個緣故,反正他在階梯上坐了下來,突然哭了出來。 半夜三更一個駝子走到雜貨鋪來,又坐下來放聲大哭,這可不是每天可以看見的事。愛蜜莉亞小姐把額頭上的頭髮推到後面,幾個男人面面相覷,很不自在。小城四周一片寂靜。 最後雙胞胎中的一個說話了:「他要不是個道地的莫瑞斯.費奈斯坦,我頭給你。」 人人都點頭附議,因為這句話是有特殊含意的。但是駝子卻哭得更大聲,因為他一點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莫瑞斯.費奈斯坦是多年前小城的居民,是個猶太人,只要你罵他是殺害基督的兇手,他就會哭,而且他每天都吃酵母麵包和罐頭鮭魚。他後來發生了不幸,搬到社會市去了。從此之後,凡是有人太拘謹討厭,或是大男人愛哭,就會被叫做莫瑞斯.費奈斯坦。 「哎,他情況特殊,」史當皮.麥克菲說,「那也是情有可原。」 愛蜜莉亞小姐只緩緩跨了兩大步,就越過了門廊。她步下階梯,看著陌生人,若有所思。她伸出一根修長的褐色食指,極其小心的碰了碰他背上的腫塊。駝子的哭聲仍未停止,但是聲音變小了。夜晚很安靜,月亮放射出柔和清澈的光芒——天氣愈來愈冷了。接著愛蜜莉亞小姐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從後面口袋裡掏出了一個瓶子,用手掌把頂端擦乾淨後,遞給了駝子喝。愛蜜莉亞小姐很少會因為心軟就讓人賒欠酒錢,要讓她免費送一滴酒給誰喝都是異想天開。 「喝,」她說,「喝了你的沙囊會舒服一點。」 駝子止住了哭聲,舔乾了嘴巴四周的眼淚,乖乖聽話。等他喝完,愛蜜莉亞小姐也慢慢喝了一口,用酒漱口,再吐出來,接著她又喝了一口。雙胞胎和工頭都有他們自掏腰包買來的酒。 「這酒很順口,」史當皮.麥克菲說。「愛蜜莉亞小姐,我從來就沒看妳失敗過。」 這天晚上他們喝的兩大瓶威士忌很重要,要不是這兩瓶酒,接下來也就沒有故事可講了。說不定少了這兩瓶酒,咖啡館根本就不會開張。因為愛蜜莉亞小姐的烈酒自有它的獨到風味,酒色清澈,在舌尖很辛辣,可是一旦進了肚子,可以在一個男人的體內發光發熱很長一段時間,還不僅如此呢。據說用檸檬汁在乾淨的紙上寫字,字跡可以隱形。可是把紙拿近火邊,字跡就會變褐色,寫下來的那句話就一覽無遺。好,發揮一下想像力,愛蜜莉亞小姐的威士忌是火,而那句話寫的是唯有男人的靈魂才知道的事情——這樣你就能了解愛蜜莉亞小姐的烈酒有多值錢了吧。無人注意的事,隱藏在黑暗心靈遙遠角落的思想,驀然間都被認了出來,解讀了出來。當織工的滿腦子只想著織布機、便當、床鋪、接著又是織布機——假設這個織工在禮拜天喝了幾口酒,遇見了一朵沼澤百合。他可以把花握在手掌心裡,細看金黃嬌美的花,猛然間心中竄過一種近似痛苦的甜美滋味。這個織工可能會猝然抬頭,開了眼似的看著寒冷的、詭異的一月天空在午夜綻放色彩,一種天地悠悠而自身何其渺小的感覺讓他在深受驚嚇之餘心臟停止。像這類的感覺在一個男人喝了愛蜜莉亞小姐的酒之後就會發生。他可能會受苦,他也可能會樂得四肢無力——但是這種經驗卻道出了真理;他的靈魂得到了溫暖,他看見了隱藏的信息。 -摘自《傷心咖啡館之歌》部份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