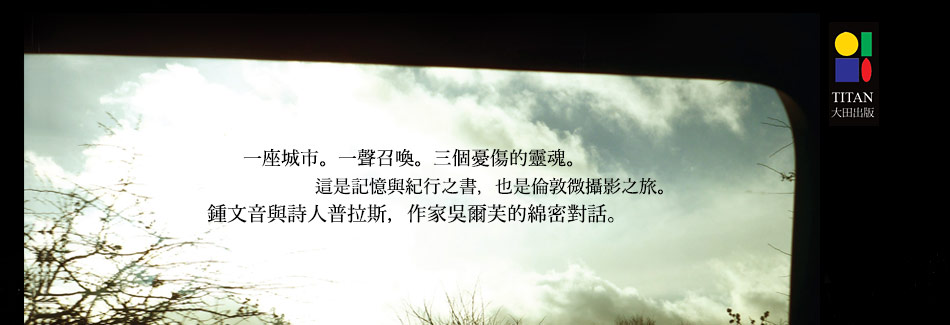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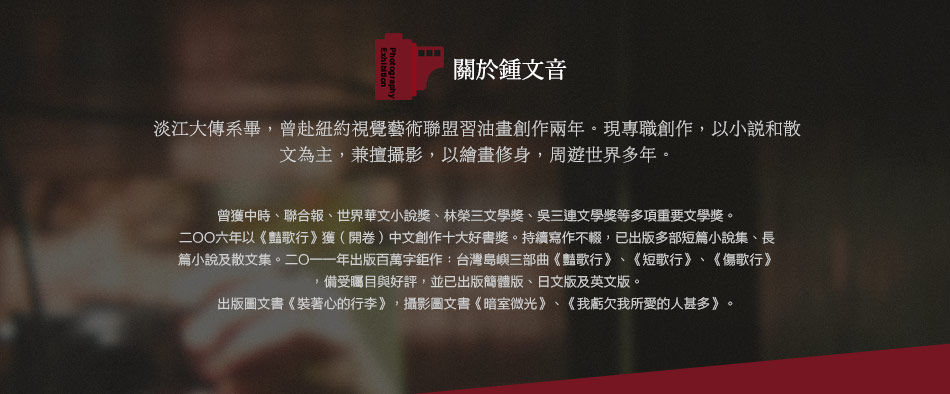

卷壹 藍眼睛與黑眼珠
她望著眼前這座深不見底的海洋,藍色的海洋引她進入夏日幻覺。
藍眼睛望著她,黑眼珠深不可測。
藍眼睛與黑眼珠,如一座山一座海。
她望著已然走到身後的那雙藍眼睛,她知道自此將帶著某些遺憾度日。遺憾不是她想用的字詞,但她忘言。
大藍深海缺氧,她總得上岸。
黑山高原稀薄,他終是下山。
荒原裡的愛情
她曾喜歡都柏林,因為喬伊斯。
現在愛都柏林,因為你在那裡。
但我離開了,男人說。
那我還是愛都柏林,她說。
我住到羅馬尼亞,男人說。
那我愛羅馬尼亞。(雖然她想說的是:我愛羅馬,廢墟與文明。)
她試著在飛機上寫著他們之前的對話,源於朗讀的交會。他覺得她用不標準的英文說話帶著一種奇異的異國情調。
記憶碎片像歷經太空爆炸,無重力飄蕩四周。
藍眼睛回想著黑眼珠的朗讀。感官的氣味,性感的聲線,帶著嫵媚的聲調,朗讀奇怪的故事。她朗讀的故事是關於氣味,一個失去嗅覺的攝影師,每天在攝影棚裡遇到來拍寫真集的女人,女體以氣味挑起他的影像感官,但卻無法挑起他的腐蝕鏽去的嗅覺。最後他得仰賴各式各樣奇異的方式去召喚儲存在記憶裡的氣
黑眼珠回憶著藍眼睛朗讀的故事:
一個旅行者在突尼斯市場遇見請他進屋喝茶的男人。西方旅者和伊斯蘭男人討論上帝存在的問題,旅者薄荷茶未喝竟,心靈卻蒙上了死亡的陰影。最後在水煙裡瞥見灰塵滿天的落日,時光已悠悠。文明的乾旱,提早到來,彌賽亞降臨也無法解決戰爭的謬錯與精神荒原的貧瘠。
藍眼睛在未抵達前,寫給黑眼珠的信:「想到死神已經做掉那麼多的人,連永恆的空氣也將戰慄不已,在一把塵土裡,人就瞥見了恐懼。」
黑眼珠在抵達前,給藍眼睛一個信息:「對現實,或有嘆息卻不哀傷,豐饒之神等待再生。」
他表面戲謔實則哀愁,她看似哀傷實則堅韌。
他曾是海明威與福克納的信徒。
她幻似莒哈絲與吳爾芙的孿生。
如蛾的呼吸
這不是她的城市,也不是他的城市。他們相會在此,戀人有著如蛾的呼吸,煽動著寂寞的夜與夜。
曾經有那麼幾年,自愛情之城歸來,旋即感染了愛的熱病,感染了不治的鄉愁。年年的冬日寒氣入侵,仍醫不了她的高燒一○三度。
她像是愛情廢墟後的荒野雜草,將短暫地陷入挨著荒牆下存息的睡眠期,將自己裹在由另一個異己的愛情唾液吐細絲所編織的回憶之網裡。
自願被俘虜似的圈禁著自己,在睡海裡潛伏,囚伏。冬日宜安寧,漂浮在無重力空間。她渴望化為他,卻多年不可得。只好入歐蘭朵的夢,好讓雌雄合體。
潛伏經久,離此刻不遠的某一年,為了終結這種說不清卻又清楚感知存在的莫名思念,她終於從無重力的愛情星船歸返大地,帶著寂寞星球赴約,開張自己的 身體帝國,任際遇帶引她上岸或者漂流。
她提醒自己要不卑不亢,但不卑不亢似乎是屬於處世的,在愛情裡少了不顧一切的激流與沖刷之美。卑微國度沒有愛情可以存活的空氣,高傲國度當然也讓愛 情失去飛翔的天空。
人應該成為自己,在愛尤是。
未見他時,她如此確定,思想如此堅毅。見了他,也許瞬間就軟弱了。
一個軟弱者,還能談什麼自己呢。
理想的自我撲殺
冷冬之日,寒流來襲,不復年輕的她處在雜沓的人群裡。她一個人自處時,通常得從別人的瞳孔裡,望見自己恆常掛在臉上的那種寂寥神色,但她想這一回或許會有所不同,她不需借助別人的折射,即可以照見自己。
因為她即將前往年輕時浪蕩過的城市,它充滿著時空差異與年華生熟的並置對撞。熟女歲月,是被自己的記憶熱燙溫熟的。
她回憶著,想像著,因距離,故連淚水,也是甜的。
但往思潮一躍,昔日年輕身影卻拼湊不起來,反而城市鮮明歷歷,泰晤士河、大笨鐘、水石書店、博物館、攝政街、唐人街、紅色雙層巴士︙︙那種常出現廣告的制式風景,很容易就會浮現腦中。細微浮動的光影,則要靠剝除外殼假象,才能一探究竟。
晚上航廈的機場擁擠著離鄉的人潮,櫃檯上的小燈光與電腦看板不斷閃爍著時間與航道,劃位小姐與行李輪軸的聲音被龐大的人潮擠壓成一只蜂箱。
蜂箱,巢穴,偏離航道的離鄉者。
眼見著城市與咖啡館逐漸換了妝,預告著耶誕節年年又將來襲的紅潮,刺目的幸福與信仰,媚俗地沾染著視覺。
文學與人生理想信仰的崩落,毋寧是她感到頹喪的根本原因。
是典型已遠?還是人理想的自我撲殺?
二○一三年她在海外時聽聞多麗絲‧萊辛過世,以八十九歲高齡仍寫作,意志力如此強悍,文學已是信仰,在漫長的文學馬拉松裡,巨人化為一座高山。她也常想起第一位女攝影家伊摩根‧康寧漢,她常還原一下旅程,想像伊摩根在九十歲時拿著笨重的單眼相機去拍那些和她一樣受時間侵蝕的老人臉孔,出版《九十之後》,她想起和同業聊過的:假使寫作只為了某些目的,或是僅僅為了博得入行的票券,那只需要動員內在一丁點東西或許就足夠了。但若像是萊辛與伊摩根則是整個生命猶如寫作大海,整個生命都在寫作的汪洋裡擺盪。
在通往機場的路程,她打了盹,夢見萊辛,夢見吳爾芙,夢見伊摩根,夢見莒哈絲……文學的高山與深海。
不真實的思念
經曼谷到倫敦。
請問要靠窗或走道?櫃檯小姐說(還好她沒戴耶誕帽)。她必須貼近櫃檯才能將聲音兜攏得清楚。
靠窗,她說。她想看離別與抵達的城市風貌,她想目睹機窗外的雲與風,離開地球的星際之子,在兩萬公尺的高空航行,如此地孤獨與奇特。轉頭就見星星,靜靜地懸浮在天際,那是否是一個個未被人類慾望汙染的淨土?
看似空蕩蕩的天際,雲朵如天床,讓飛機如夢奔馳。飛機依星圖前進,速度讓她不斷地靠近異鄉。愛爾蘭男人正在羅馬尼亞的家裡打包著行李吧,十小時之後,他緩慢地登機啟航,都能比她早一步抵達,他將蛻變成藍眼珠情人。
她一向思緒亂竄,忽焉想起文成公主與尼泊爾公主,兩個女人同時間欲嫁給藏王松贊干布,但居長安的文成公主,花了三年才抵達西藏,漫長的旅途裡只有風沙與孤寂,還有小小的經書與佛像。另一邊的尼泊爾公主緩慢地準備著嫁妝,她也帶著佛經與佛像,但三個月她就來到了藏王的身旁,她早一步抵達,忽然就成了正室之感,而尚在旅途的文成公主不知自己受盡千辛萬苦所抵達的國度已經有人比她先馳得點。
距離成了戀人的障礙,距離考驗堅貞者的恆心,而她是個意志薄弱的人,尤其對愛情缺乏信念。
離台前,她去了一座大學講座,入夜落腳學人宿舍。在校園遊走時,被一陣如浪的原住民聲音給吸引,由於校園寬廣,一直找不到路徑通往的迷航狀態。待抵達時,癡醉如浪的渾厚之音卻已轉成尖叫嘶吼。原來如浪的潮聲是求偶之歌,之後是搶婚戲碼。
彼時頓然失落。
就像現在,她已看見分離畫面的失落。相聚就看見分離的預言,但她和他皆渴望這不易的相聚,因不易,故相聚的本身就存在著美好,這美好足以沖刷分離後在陌生城市的孤單。
他說:「我知道這次若錯失了妳,將會是我生命版圖的一塊永恆缺失,雖然我並不知道我缺失了什麼。」
不知旅程結束,她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彌補他生命中的那塊缺失?
那是什麼樣的缺失?她不知道,遺憾憂愁哀嘆不捨︙︙在拉著行李箱時,漫過無數的念頭。
實情是她早已不那麼需要他了,甚至可說不那麼需索情愛了。在佛法中心幾年的學習,也就是在清理這些心河阻塞與陳積的東西。然而幾年過去了,歷經幾次的情愛考驗她都節節敗場。明知不動聲色是藥,但她的心不僅拒絕服藥,且還大動聲色。
啟程前,看見就要敗陣下來的自己,那是很奇怪的輸家之感,因為征戰的對象其實也是自己。
明知情愛成幻,但她願意為他赴約,就光憑一種靠近意志美學般的等待。等待被賦予高貴,因為人總是善變。出現不變的等待,人才有了點真心。

| 10445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26巷2號2樓 電話 : 02-2562-1383 E-Mail : titan3@ms22.hinet.net |